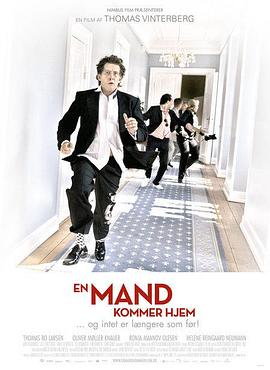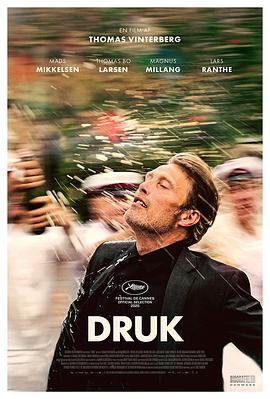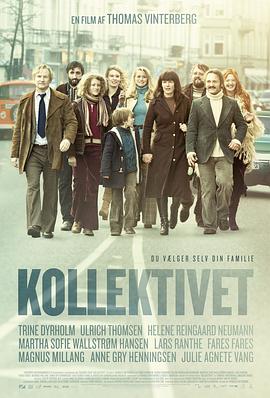剧情介绍
文:宿夜花
20世纪60年代的奥斯卡颁奖礼上,英国古典文学与历史题材的电影,与英国电影新浪潮、新好莱坞时期盛行的现实主义题材(例如《毕业生》)影片交相辉映。从《窈窕淑女》、《良相佐国》到《雾都孤儿》,奥斯卡最佳电影大奖授予英国古典题材,似乎是好莱坞最稳妥的选择。
这种英式古典题材的复苏,自然是与电影发展的时代环境密不可分。60年代的英美影坛处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之下:
冷战与核威胁造就的阴云密布的动荡局面;
性解放运动、迷幻摇滚嬉皮文化构成了青年文化的潮流;
第三次科技革命在信息、新能源技术上的突破,革新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与认识世界的方式,却给人带来了更多的未知与隐患。
因此,古典文学题材影片不仅描绘着传统人文图景,其中更透露出对回归自然的渴望、对工业文明尚未波及前传统农业生活的呼唤。电影《远离尘嚣》正是这一时期古典题材的代表,改编自作家托马斯·哈代的同名小说。影片宣扬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那田园诗般的美好、安详、静谧、诗意,似乎不沾染一丝现代工业文明的冰冷、残酷、枯燥、繁杂,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
而电影中通过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悲剧书写,又于呼唤生态自然观的同时,兼具女性主义角度的探索意义。在此,先通过阐述女性形象的突破与局限,再进一步窥探影片背后所寄托的生态理念。
注:电影《远离尘嚣》的主演朱莉·克里斯蒂、导演约翰·施莱辛格是60年代颇具影响的英国电影人,前者用《亲爱的》获得了奥斯卡的最佳女主角、后者凭借《午夜牛郎》获得了奥斯卡的最佳导演。
01.女性主义的探索——芭思希芭形象的突破性
电影《远离尘嚣》中的芭思希芭(bathsheba),比之维多利亚时代传统女性的克己复礼、保守克制、含蓄隐忍,从外在的行为仪态到内在的性格内核都具有一定的突破性。从言行举止到行事风格,芭思希芭对传统男权社会驯化的女性仪态规范(温顺娴静、优雅贤淑)表现出的反叛性是不言而喻的——她特立独行、举止张扬、不受约束。
她的农场女主人身份,使得她完全不用依附于任何男性生存,她拥有自己安排、选择自己生活方式与爱情婚姻的自主权——她不再是被男性凝视、男权异化的对象,拥有对男性同等的审视与选择的权力。影片通过三个男性角色的对照映衬,来完成对女主人公性格的全面刻画。
首先是牧羊人加布里埃尔·奥克(gabriel oak),他的性格忠诚、仁厚,对待人生勤勤恳恳、心怀感恩与怜悯之心。面对奥克的追求,芭思希芭从未放于心上,她不想被婚姻的关系禁锢、也不想被妻子的身份束缚。
其次是农场主波德伍德(william boldwood),他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与物质条件,个性沉稳、理性、平静,是世俗层面上芭思希芭最体面的恋人。在芭思希芭的一场恶作剧(写一封“merry me”的情书示好)后,他的古板压抑、自我约束维系出的一种平衡的心境,被打破。他在爱而不得、追求而无果的心理创伤中一步一步走向毁灭与癫狂。
最后是中士特洛伊(sgt. troy),他的性格变幻莫测、诡谲无常,他展现出不同于传统道德法则信奉者(牧羊人与农场主)的自由个性,正因如此俘获了芭思希芭的芳心。而当他们完成了婚姻之后,却发现特洛伊性格上的致命弱点:恣意妄为、无拘无束、傲慢自负,他纵情声色、投注大量金钱用以赛马玩乐,却对农场全无责任。特洛伊辜负了恋人范妮,却无法真正发自内心地爱上任何人。
电影《远离尘嚣》通过芭思希芭的爱情选择与对待婚恋的态度,试图探索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困顿于传统宗法思维桎梏之下的女性,在女性意识逐渐觉醒中的自我个性与意志的追求,具有一定的女性主义价值诉求。但与此同时,电影中的女性,挣扎于传统田园社会与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之中,成为多重矛盾的牺牲品。
02.保守结局中的时代局限性与新时代女性的思考
电影的结局,芭思希芭的丈夫特洛伊,被气急败坏的波德伍德枪杀,惊慌失措的芭思希芭,最终又屈服于现实的困境,最终选择与奥克成婚。这无疑是非常具有设计感与象征意义的情节编排,芭思希芭的自我意志追求,冲撞了传统农业文明社会的男性利益,因此她陷入了疲于应对的精神困境中,芭思希芭最终选择回归传统婚姻来获取一种世俗生活中的安稳。
这种结局,体现了故事原作者托马斯·哈代的一种保守价值观。即是说将回归传统田园宗法社会(奥克一角代表着传统的爱、奉献、宽容与慈悲)作为矛盾的想象性解决方案,却无法深入挖掘这种传统形态对女性价值的束缚扭曲以及更多劳工阶层女性的悲剧根源,这不失为一种时代局限性。
从反叛男权到皈依父权,在妥协与屈从中,芭思希芭收获了传统意义上的幸福,但无疑是彻头彻尾的悲剧——以丧失了自由精神与自主意志为代价。芭思希芭的悲剧既有时代因素,也与个人的性格弱点相关。
一方面,芭思希芭人格独立与自主的前提,来自于经济上的自由,而实现这种自由的经济基础,正建立在男权社会的财产继承之上——她通过继承叔父的农场来获取合乎传统宗法思想的社会地位与稳定的物质财富。而对于更多的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她们无法通过公正合理的社会分工、自身的才干和智慧来获取经济独立。
另一方面,芭思希芭不拘泥于陈规陋习的自立与挣脱传统桎梏的自由,很大程度上沾染着虚荣与利己的心理。因为自己一时兴起的恶作剧(书写一封虚情假意的情书),她唤醒了波德伍德内心压抑已久的爱情欲望,而对波德伍德的精神世界的负面影响,她一直选择漠视与逃避。无论对于农场主波德伍德、抑或是牧羊人奥克,她总是看重眼下的利益而缺乏真正的爱与尊重。
因而,女主人公芭思希芭纵使拥有看似自由、不受约束的性格,却无法被视作完整意义上的独立女性。正因如此,在当届的奥斯卡奖上,饰演芭思希芭的朱莉·克里斯蒂未能获得最佳女主角的提名。
而在两年后,格兰达·杰克逊在《恋爱中的女人》中饰演的古德兰一角,诠释出了现代价值观下独立女性的真正内核——两性之间的自主自立建立在平等尊重之上,女性的价值实现来自于才学与智慧、自我的独特个性与豁达通透的人生观,因而收获了从影评人到奥斯卡等各大奖项的最佳女主角。
03.生态自然观的呼唤
女性如何在世俗枷锁下寻找心灵的自由?这是影片所诞生的60年代以及故事背景中的维多利亚时代,所未能给予实质解决的问题。而影片在引发对工业文明中现代女性价值思索的同时,将这个问题置于一种回归自然的生态理念之下,这也是60年代英国古典题材影片中所常见的手段,例如同一时期肯·罗素执导的电影《恋爱中的女人》(改编自戴维·赫伯特·劳伦斯同名小说)。
影片运用了大量的大全景、空镜头,去呈现威塞克斯乡村原始风光的宏大壮丽、粗犷浩渺,导演强调四季变换的自然规律、变幻莫测的自然环境给人生活的影响,昭示一种对自然力量的崇拜心理;对农民劳作的田园生活,赋予了一种幽默乐观又诗意和平的心态——劳动者与大自然保持着一种安然自在、怡然自得的平衡。
在工业化的初期,这种对机械文明破坏自然生态的批判、质疑,回归自然是一种合乎传统心理的解决之道;因而女性主义的探索也没有触及到女性群体的话语弱势,以回归自然田园生活的责任、仁爱、慈悲作为一种理想式调和。
电影《远离尘嚣》对生态自然观的诠释是不够全面,停留在单一维度的渴望回归自然、留恋传统田园生活方式。
事实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并非是需要完全幻想昔日乌托邦式的田园诗、沉溺在一种过往的安逸模式中故步自封、因循守旧;改善传统生活方式中不合乎人性的陈旧、闭塞、迂腐的思维观念,释放出被传统陈规陋习禁锢的天性,才是一种动态、发展、辩证的生态自然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