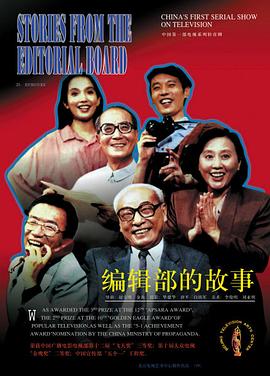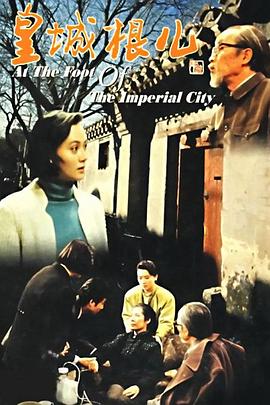剧情介绍
1992年1月到2月,已经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88岁高龄的邓小平,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等地,35天行程6000公里。他一路走,一路说,发表了掷地有声的系列“南巡讲话”。
1992,移动电话刚刚传到中国,全国才一万八千部,又黑又大像块砖头,一个卖三万元,只有最富有的人才用得起它。文化衫飘荡在中国的城市街头,“烦着呢,别理我”“真搓火”“不会来事”等充满情绪的句子被人们背在身上招摇过市。这一年4月,北京王府井大街南口和长安街教会的地方,矗立起一块“麦当劳”的招牌,黄底红字的“m”标志着世界快餐连锁巨头进驻了中国商业的黄金地段。
这年5月,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价格全面放开,来自全国各地人会聚上海疯狂抢购“股票认购券”。同样的故事发生在深圳,一个维持秩序的警察抱怨说:“我嗓子喊哑了,衣服湿透了,没有用!这简直就是一群野牛!”体操王子李宁下海了,“林妹妹”陈晓旭下海了,34岁的王朔也投身市场大潮。他纠集了刘恒、莫言、魏人、刘震云等一批作家,组建了“海马影视创作室”,明码标价,专事剧本生产。
这一年,张艺谋拍摄的《秋菊打官司》在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金狮奖。在这部近乎“原生态”的现实主义电影的掩护之下,张艺谋之前拍的《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也一并拿出来放映。这些充满浓烈色彩和民俗奇观的艺术电影,奠定了张艺谋中国首席导演的地位。
年初,中国国奥队在新加坡默迪卡体育场遭遇“黑色九分钟”,在打平就能前往巴塞罗那的大好形势下被韩国人灌了3个球。主教练徐根宝成了众矢之的,回国之后不但从国奥队下课,他通过竞聘得来的国家队职位也被剥夺。愤怒的球迷不再相信国产教练,中国队迎来了史上首位外籍主教练——施拉普纳。球迷亲切地称呼这个德国老头为“施大爷”,期待他能把屡战屡败的中国足球队带进世界杯的殿堂。
这一年有一部儿童剧不能不提。六一儿童节那天,中央电视台制作的52集电视剧《小龙人》开播。三个带着古怪想法的孩子唤醒了沉睡几千年的玉龙,小龙人开始了寻找妈妈的漫长旅程。这部剧中密集地穿插着儿歌,听着这些歌长大的人们到现在都会不经意间哼唱起“就不告诉你”的旋律。
在一种士气如虹的氛围中,中国进入了1993年。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一年前还处在尖锐交锋、裹足不前的中国,一年后出现了经济过热的明显迹象。通货膨胀卷土重来:大城市的物价指数涨了17%,原材料价格长了40%。世界银行的专家们向中国政府发出警告:“这些现象如不及时制止,可能演变为一场金融风暴”。
这一年,有很多人处在膨胀失控的状态中。天津大邱庄那位自以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庄主”禹作敏被抓了起来;辽宁的中长跑教练马俊仁指挥弟子不断刷新世界纪录,随后也因为奖金分配和粗暴管理的问题,与弟子们关系破裂。
这一年,萦绕在很多中国人心中的“美国梦”因为一部电视剧的播出而不再那么光鲜美妙。此前,大洋彼岸先进而富足的美国对中国人形成了致命的吸引力。除了公派出国,大多数人都是自费出国留学。以留美生活为题材的《北京人在纽约》开播,观众惊奇地看到:美国并不是所有人的天堂,也有不少中国人在这里沉沦、迷失,陷入了经济和精神的双重窘境。来自出国签证机关的数据表明:《北京人在纽约》播出后,大城市里选择出国的人数有所下降。
(1)失落的“美国梦”
顾名思义,《北京人在纽约》说的是北京人在纽约奋斗与挣扎的故事。在家庭的分解与重组中,在婚外情的发生和发展中,在移民子女的教育及两代人的观念冲突中,这群做着“美国梦”的北京人,事业与情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故事说的是,大提琴演奏家王启明来到美国,经过艰辛的奋斗,成了一位富翁,他的感情却世界却发生了严重的倾斜。妻子郭燕成为外国商人大卫的妻子,大卫是王启明最大的商业竞争对手。王启明也有了温柔可人的红颜知己阿春,但是女儿宁宁的到来,在几个人的生活中掀起轩然大波。宁宁不能理解父母亲,更不能接受阿春,她变得任性和反叛,以放纵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父母的怨恨。
《北京人在纽约》细腻展现中国人在美国的生存状态,一开始,片子里就说:“如果你爱一个人,把他送到美国去,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也要把他送到美国去,因是那里是地狱。”郑晓龙说:“《北京人在纽约》来自于曹桂林写的同名小说,当时中国出国热,大家就觉得国外什么都好,想到国外去淘金。确实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和思想解放程度,跟国外比有巨大差别。你在飞机上看美国,纽约灯火阑珊,飞回来到中国底下黑糊糊一片,和美国差距非常大,所以当时很多人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到国外去。中国人有一个传统思想就是衣锦还乡,在外头无论怎么样,回国要表现出在国外特别好。其实我了解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有很多人在国外餐馆里打工很苦,攒点美元回到国内来摆谱。但是很多人并不了解国外的情况,认为国外遍地黄金,《北京人在纽约》写的是他们在美国奋斗的不容易。当时有人跟我说,这个片子带着全体中国人们出了一趟国,了解了原来美国是这样的。”铁的事实总是比空洞说教更有力量,《北京人在纽约》播出以后,出国热趋于冷静。
《北京人在纽约》1992年拍摄,1993年播出。开机之前,导演郑晓龙到美国体验生活,想收集素材,充实一下比较单薄的小说。他到美国之前信心满满,觉得这件事并不太难,可是去了以后座谈会开得越多,了解的情况越多,心里就越没底。因为去美国的人情况非常不同,有留学去的,有移民去的,还有偷渡去的。留学的也分国家派的,自费去的,情况各异,结局各不相同。郑晓龙苦于不知道该表现哪一部分人的生活,就想尽量表现更多的阶层的人,就觉得千头万绪,难以定夺。直到有一天,他突然醒过味来:“我管他是哪一类,我只管他是不是真实的,王启明这一个写好最重要。”
郑晓龙回国以后着手修改本,前四集还有小说的内容,四集以后就没了,另起炉灶。小说里面王启明和郭燕没有离婚,电视剧到第四集就让他们离了,郭燕和大卫住一块去了,王启明自己一个人了,两条线齐头并进。《北京人在纽约》一开始就确定要突破华人圈的故事,一定要直接面对美国人,直接表现种竞争性和文化差异,这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中非常少见。里面有一些词既机智又隽永,比如王启明说:“你们美国人总喜欢把脚插到别人的家里去”。戴维就说:“你们中国人总喜欢把家搬到我们美国来”。
在剧中,姜文扮演了男主角王启明,这是他唯一一次出演电视剧,就奉献了一个情感丰富、血肉丰满的形象。女主角阿春的扮演者是王姬,这位八十年代的北京人艺演员当时已经出国经商。阿春的角色能落在她的头上,完全是阴差阳错的结果。王姬回忆说,“我回国探亲碰到陈道明夫妇,介绍我认识冯小刚。他们就拍了几张照片,说我们角色选了胡慧中,说以后有机会再合作吧。一个月以后突然跟我打电话,说胡慧中没谈成,王姬你能不能来?实际上我已经开始在美国做生意,但我还是一口就答应了,因为我想演戏,就像干枯的土地等待着雨水的滋润。我觉得这可能是命运的安排,所以我至今非常感谢陈道明。我因为在那边生活过,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再加上过去演过戏,再加上他们实在着急没人了,就让我又加入了这个团体。当时有记者采访问我说,你跟姜文演戏有压力吗?我说为什么有压力,我说我比他熟悉那边的生活,我说我演的就是身边手到擒来的人,我随便想一个就能把它表现出来,一点压力都没有。”
可是导演郑晓龙的心头那时却充满压力。为了拍摄《北京人在纽约》,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从中国银行贷款150万美元,130万美元带到美国用于前期拍摄,留20万美金在中国用于后期制作。当时,电视剧还没有完全市场化,《渴望》花102万拍了50集,只回收了50多万,赔了。《编辑部的故事》花了150多万,回收了大概90多万元,还是赔。为了拍《北京人在纽约》,郑晓龙到处融资,好不容易才拿到这笔钱。
王姬回忆说:“我觉得郑晓龙和冯小刚那时非常认真,他们是输不起的,这么一个题材在海外第一次拍摄,形成一个里程碑。他们光选演员就选了多少个来回啊,在很多问题上做到了极致。我参加了那么多电视剧的拍摄,没有任何一个电视剧组能够这样做。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两个组,冯小刚带一组,郑晓龙带一组,回来两组拍的东西,大家晚上在那看回放,除了看回放有没有质量问题,那是一个竞争啊,看完a组拍的东西,再看b组拍的东西,真的好就给鼓掌,不是刻意鼓掌,看完之后都知道,应该这么拍,第二天就调整。这种工作态度必定奠定了它的成功,这是必然性。”
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虽然所有人都认真工作,但有些时候只能将就。按王姬的说法,阿春就不应该开一个道奇车,在美国开餐馆的人不是宝马就是奔驰,道奇车不符合阿春的身份。郑晓龙据实回答:对不起,没钱,宝马车租一天一两千美金,这个一两百块就搞定了。好在,这些小的环节虽然失实,但国内的观众看不出来。
在一种良好的创作氛围中,主创人员已经预感到这部戏的不同凡响。剪片子的时候,冯小刚就对王姬说:“你要火了”。后来,《北京人在纽约》播出时,观众们的出国热情受挫,却喜欢上了剧中善解人意的老板娘“阿春”,王姬在一众演员中的受欢迎程度也最高。王姬说:“演员塑造角色,离不开你自身的东西,包括你的价值观,你的好恶取舍,你的语气和态度,我觉得阿春身上有我身上的影子。比如善解人意,因为我本身就是善解人意。我除非有意得罪哪个人,我从来不会在任何场合去故意给人家难堪。好多东西是潜移默化,融在角色里的。”
同样受到欢迎的还有刘欢作曲、演唱的主题曲《千万次的问》。郑晓龙说:“用不用《千万次的问》做片头曲,我还犹豫了好长时间,我觉得一开始先声夺人,跟我的性格不大相符,后来想想一下带进去吧也可以,最后定的就这样。这个片子里面中英文共同来用,如果你不懂英文的话,作曲恐怕会有点问题,所以用了学外语出身的刘欢。刘欢当时没有成名的任何作曲,我们剪片子住在友谊宾馆,用了三个多月,刘欢住了两个多月,我们经常剪完片子回来就到他房间听听他做的曲。刘欢是《北京人在纽约》剧组里面唯一没有去过美国的,其他大家都去过。当然他歌唱的不错,但是作曲从来没有过。也挺有意思的,没干过都干成了。”
《北京人在纽约》拍完,中央电视台并没有直接给现金,而是采取了广告交换的方式,每集给剧组5分钟的广告。《北京人在纽约》原来是20集,后来变成21集,每一集要压缩五分钟出来给广告,然后才能够还银行的贷款。最后算下来,还钱之后,这部片子还赚了几十万元。郑晓龙清楚地记得,向银行还完钱的那天,他开车回家时浑身发冷,到家就发烧,“我把这个事做完了,心里一下松下来了”。
以现在的眼光看,《北京人在纽约》不仅把真实的留学生活摆在了国人眼前,有力地干预了社会潮流,更重要的是,它开创了贷款拍电视剧的新模式,为这个方兴未艾的产业进行了披荆斩棘的探索。此后,电视剧产业化的步伐不可阻挡,来源各异的资本流入这个市场,中国电视剧逐年增产,日渐兴旺。
(2)不老的《过把瘾》
这一年冬天,一部非黄金时段开播的感情剧《过把瘾》慢慢热了起来。这部剧深入地揭示了婚姻与爱情的甜蜜和苦涩,很多人从杜梅和方言这对欢喜冤家的分分合合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当全剧以方言身患怪病不久于人世的悲剧收尾时,无数观众的心被一种“珍惜身边人”的紧迫感所把持。
1993年冬天,在老家过寒假。
有天晚上快十一点了,晚间的体育新闻都播完了,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停在了中央一套上。电视里一个麻杆儿般的小伙子和一个长相很普通的女的在街上接头。当时并不知道王志文和江珊的名号,只觉得男的很面熟,好象是《皇城根》里骑摩托的那个不负责任的坏小子“王喜”,女的则全无印象。麻杆儿说话很冲,张嘴就是“出门照镜子了没有?怎么打扮得跟鸡似的?”女的穿了一身黑红相间的裙装,长长的黑色丝袜,听了这话扭头就走。这就是我跟《过把瘾》的第一个照面。方言和杜梅相约去方言父母家,因为穿着发生了纠纷,一吵就把我吸引住了。方言死活也不肯说出“我爱你”三个字,杜梅为此竟把他绳捆索绑,并在其脖子上架上菜刀。然后就离了,离了却仍然像后来流行的男女合租一样住在一套房子里。还在吵,但吵架的方式变了,有理有利有节了。我很纳闷:这么好的剧为什么放在了这个夜猫子出没的钟点?酒香就不怕巷子深吗?
这还真是这部剧的首播。不过,央视这么糟践东西,《过把瘾》还是火了。第二年的五一期间,我又看了一遍《过把瘾》。当时我们宿舍里放着一台打游戏专用的黑白电视机,偶尔也发挥一下本职功能。我生病发着高烧,投入地沉浸在剧情中,听刘欢唱“意念中的热热呼呼”,就更加迷迷糊糊,神志不清。我当时已经熟读王朔,看完就知道,这是根据他的三部小说《过把瘾就死》《无人喝彩》《永失我爱》改编的。《过把瘾就死》和《我是你爸爸》《动物凶猛》一样,肯定是王朔的传世作品,它把男女豪猪“因为寻求温暖而相互靠拢,因为刺伤对方而互相逃离”的理儿琢磨透了,下笔也狠辣锋利,不留情面。《无人喝彩》则是电影剧本,甜不滋儿的挺好玩。《永失我爱》纯粹是个煽情的一袋烟小说,“肌无力”要了小伙子的一条命,也要了女青年的半条命。三部小说天衣无缝地连缀在一起后,产生了浑然一体的全新感觉。我当时喜欢方言的说话方式,听着还是王朔式的出奇制胜,可是不那么“话痨”了,一句就够人乐半天,或者顶得人半天出不来气。我也喜欢杜梅,她的眉飞色舞让我的心里春色无边。那时江珊还是中戏的学生,据说赵宝刚选中她是因为她长相平常。要不怎么说各花入各眼呢。
现在想来,这两个感受就是《过把瘾》的精华所在了。方言的口才那是王朔的余响,智慧而招笑。为杜梅着迷那是因为自己处在多情的季节,对爱情的电流格外敏感。这么多年过去了再看这部片子,方言的口条仍然很顺,因爱中招的感觉却找不到了。这充分说明,只有在特定的年龄和心绪中,才能被影视里的爱情打动。这跟“珍珠翡翠白玉汤”的道理相通。
谈到为何拍摄这部感情浓烈的电视剧,赵宝刚说:“进入九十年代中期之后,人们不满足于仅仅是带有传统文化特征的东西了,需要一种新的表达方式。《皇城根》是传统理念根深蒂固,又揉进了一些现代意识的一部戏,我发现人们对于传统理念开始排斥,恰恰喜欢那些新的青年形象,结果褒贬不一,有的说惨不忍睹,有的说精彩绝伦。我就做了一年的思考,发现这个年代需要一种情感的寄托,我要拍摄今天的情感。我找来找去,选中了王朔的三部小说:《过把瘾》《无人喝彩》和《永是我爱》,结合在一起弄了《过把瘾》。你们可以查一下,在这个之前中国没有纯情感戏,多多少少还带有一些人物命运、政治色彩这些东西,《过把瘾》是第一部,而且这种尝试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之前,赵宝刚一直是领导让导什么就导什么,《过把瘾》是他第一次自己选择题材。赵宝刚把自己的观察和生活都给放进去了:“我、郑晓龙、冯小刚、王朔,我们四个人的媳妇的影子,都能在片子里看见。再加上男女相处到一个时间段,会出现情感枯竭期,说的就是这个。”这部戏的成功增强了赵宝刚的信心,他觉得《过把瘾》是90年代青年恋爱婚姻的一个缩影,所以得到了极大的共鸣,但它只是表现这些东西,没有一种对社会的“带动”感,于是又导演了王志文、许晴主演的《东边日出西边雨》。这是争议非常大的一部作品,观众普遍认为“这不是我们的生活”,是一种美好生活的想象。但赵宝刚通过这部剧确立了自己的方向:“不管说好还是说不好,起码都认为我们北京很美,北京的秋天很美,里边的人很美,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有影响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追求这种浪漫的东西。”
这个追求体现在他后来的一系列作品中。1996年的《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是海岩编剧,徐静蕾初登荧屏扮演的女警吕月月打动了观众。对吕月月来说,潘小伟是情,小提琴是义,失去了潘小伟,感情难以承受,拿不回小提琴,又完不成任务。她在这个矛盾交错中徘徊,直到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无雪的冬天》平淡过渡后,赵宝刚迎来了他的颠峰之作:《永不瞑目》。这部戏仍然是警匪题材,仍然是一个“卧底”的挣扎痛苦。不同的是,女警察换成了男大学生。故事传奇,感情真挚,歌曲煽情,演员形象出众,这部剧成了1999年最火的电视剧。
之后,不管是年代戏《像雾像雨又像风》,还是当代戏《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不管是《别了,温哥华》的留学生题材,还是《奋斗》的八零后奋斗史,赵宝刚总是保持着唯美浪漫的艺术格调。
赵宝刚对大众的欣赏需求有着精确的把握,在选择题材上非常敏锐,从王朔的幽默语言加情感刨析,到海岩式的警匪追逐、情义两难,再到石康的新新人类、爱恨由己,他都能用精美的影象表现出来,每拍几部戏就能推出一部大热之作。
(3)最早的偶像派
《过把瘾》的热播,捧红了王志文和江姗。王志文不是英俊小生,但“方言”外冷内热的个性和当代浪子的气质,是当时的年轻人最欣赏的。而江姗的眉飞色舞和轻嗔薄怒也相当讨喜。两个人其后还合作演唱了该剧的片尾曲《糊涂的爱》,拍成mv在电视台反复播放。那时候还不流行“偶像”的说法,但以他们的人气而论,也可以说是最早的偶像派。
王志文在之前已经演了很多片子,这部戏让他冲上云霄。王志文说:“关键是剧本好,没有废话,无可挑剔,之所以现在还有人津津乐道,就是因为写了男女之间不变的情感。我和江珊第一次配戏有点偶然。我1988年分配到中戏任教,本来要带她那个班,因为我可能不太爱好教学工作,没带成。但我们认识了。宝刚是我好友,他要拍《过把瘾》,要找个有感觉的女演员演杜梅,我说她不错。大家见了一次面,就这么成了。”
其后的十几年间,王志文修炼成了中国最具爆发力和表演弹性的男演员。他能演《刑警本色》里的瘦削但气势逼人的警察萧文,也能演《墨攻》里的无道昏君梁王,既能演《黑冰》里性格复杂的毒贩子,也能演《国家干部》里眼里不揉沙子的好市长。
戏里的方言颇有点浪子气质,生活中的王志文也不是“省油的灯”。王志文1984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在校结识了长他两级的林芳兵,发展了一段校园恋曲。林芳兵早在八十年代就已是明星,她最著名的角色是陈家林导演的电视剧《唐明皇》里的杨贵妃。1988年的夏天,王志文从电影学院毕业,与女演员潘婕相识、相恋。潘婕是老影星黎莉莉的外孙女,她承认与王志文有过“很单纯的感情”。1990年前后,徐帆在中戏上学期间,曾是中戏教师王志文的恋人。1991年,王志文与许晴参演了潘小杨导演的电视剧《南行记》,后又合演赵宝刚导演的《皇城根》,开始了一段著名的恋情。俩人分分合合,好比他们主演的热门剧《东边日出西边雨》。如今,这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2008年,42岁的王志文与小他十多岁的金领陈坚红在上海成婚,不久后喜得贵子。
在《过把瘾》片头中,赫然写着王志文和江珊“领衔主演”,这在以前是港片的专利,内地还是头一回见。接下来的“主演”是四个:“潘佑军”赵亮,“贾玲”刘蓓,“钱康”李诚儒,“韩丽婷”史可。刘蓓和李诚儒这十几年来老有叫得响的作品。《过把瘾》之后,刘蓓的星路和冯小刚紧紧联系在一起,刘蓓当时的先生张黎则是冯小刚的御用摄影师。在冯氏贺岁片开山之作《甲方乙方》和冯氏带有自传性质的婚恋片《一声叹息》里,她都是女主角。后来,张黎闯进电视圈成为重要的电视剧导演,刘蓓主演了他的《军人机密》。
八十年代初,李诚儒最初曾在央视的《西游记》剧组里做剧务,是杨洁导演手下的得力工作人员。后来下海经商,倒腾服装,但心里还惦记着演戏。后来,他遇到自己学表演时的同学赵宝刚,以客串的形式开始拍戏。通过《编辑部的故事》和《过把瘾》,李诚儒在圈里站稳脚跟,于是下定决心停下生意,重新成为一个演员。
赵亮是一个优秀的话剧演员。在国家话剧院出品的《叫我一声哥,我就泪落如雨》中,他和刘威演一对儿患难兄弟,说的是金钱惑乱人性的事。在林兆华导演的话剧《厕所》里,他演一个看厕所的工人。这个戏结构类似于《茶馆》,以厕所为舞台反映世道的变迁。此外,他演过电视剧《玉观音》里的刘明浩、《射雕英雄传》里的老顽童,都是不太抢眼的配角。《过把瘾》里的潘佑军是个婚姻失败者,他是方言的军师,也是方言的镜子。他一张嘴就带彩儿,跟“玛莎”那段爱情最有喜剧效果。
史可是巩俐在中戏的同班同学,她长相洋派,却把小有心计的家常妞“韩丽婷”演得很到位。《四世同堂》里汉奸冠晓荷的扮演者周国治,演了方言单位的“主任”。他阴着个脸,老想说方言两句。他“吱喽吱喽”地喝着茶,方言恨得牙根儿发痒。喜剧演员常兰天演了方言的邻居,小心翼翼地上来请他把不要用噪音扰民。
(4)强悍的笔杆子
王朔小说改编电视剧不多,因为他的长篇不多,中短篇居多,更适合电影改编。郑晓龙早年间拍过王朔的《空中小姐》,再就是《过把瘾》,《编辑部的故事》《爱你没商量》《海马歌舞厅》都是直接写的剧本。王朔通过影视影响大众,瓦解了正襟危坐的保守观念,改变了人们看世界的视角。
需要大说特说的是编剧李晓明。一般人光知道《过把瘾》是王朔的作品,岂知李晓明的功劳一点儿也不小。首先,王朔的创作本就受李影响甚大,比如《你不是一个俗人》中扮成巴顿将军过把瘾的创意就来自李晓明,后来被冯小刚拿去拍了《甲方乙方》。“会弹巴赫的盖世太保风度翩翩地去拜访巴黎市民”也是李晓明的段子。再说,《过把瘾》从王朔小说变成电视剧,味道已全变了。语言狂欢没了,俏皮话一句是一句了。小说里的刺痛感没了,王朔笔下方言和杜梅的婚姻是愁云惨雾的、绝望无解的,但到了李晓明和赵宝刚这儿就成了不伤大雅的纠纷和玩闹,分分钟就能雨过天晴。把《无人喝彩》加进来,消解了《过把瘾就死》的残酷气息,过完瘾以后不死了,经历风雨后见着彩虹了。把《永失我爱》加进来,为了悲剧而悲剧,着实赚足了观众的眼泪。说白了,三部王朔加起来已经不是王朔,赵宝刚和李晓明完成了对王朔的大众化改造。
李晓明是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资深编剧,33岁时写了《渴望》。二十年来,他一直在写,《过把瘾》、《北京人在纽约》、《像雾像雨又像风》、《东边日出西边雨》、《一年又一年》、《欲望》……,500多集,1000万字,全部投拍,把把有响。这样一个功勋编剧,做人却尤其低调。有人这样描述他:“多年来,此人对外提供的手机号码、呼机号码不过是一串毫无意义的该死的数字。除非他想找你的时候。这家伙一直令许多找他的人牙齿痒痒”。 他自己的说法是:“我喜欢自由的生活,在家呆着是常态,喜欢和自己较劲。作为职业编剧,就像装修公司,以不变应万变,什么题材都要写,但不能太机械地体验生活,要保持一个和普通观众一样的心态。”
有意思的是,由于当时的保守派对王朔作品中的“痞气”心存忌惮,《过把瘾》被放在了晚上十点半后播出。然而,真正的好东西是不怕“穿小鞋”的,观众从大量的电视垃圾中精确地发现了这颗珍珠,进而形成了罕见的“午夜效应”。这件事可以视为一个冷冷的提醒:以导师自居是一件可笑的事情,大众总能突破重重阻力找到自己中意的东西。
文/李星文
版权声明:微信公众号【影视独舌】所有原创文字,版权均属【影视独舌】及原作者所有。欢迎分享至朋友圈,但如有其他媒体复制转载,需征得我们同意并注明出处。
喜欢本文就点击右上角分享吧!
搜索微信号“dusheme”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回复“独舌群英汇”加入独舌的微信讨论群,与各位影视爱好者一起畅聊!
【影视独舌】
由资深媒体人、影视产业研究者李星文主编,提供深度的影视评论和产业报道。高冷、独立、有料,助大家涨姿势、补营养、览热点。涵盖微信、微博、博客、豆瓣和人人小站、网站五大载体。在今日头条、新浪、网易、腾讯、搜狐都有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