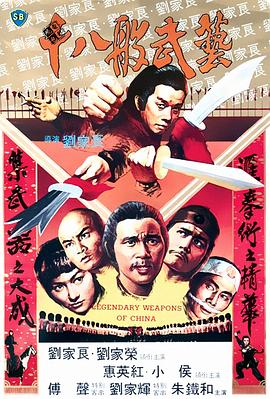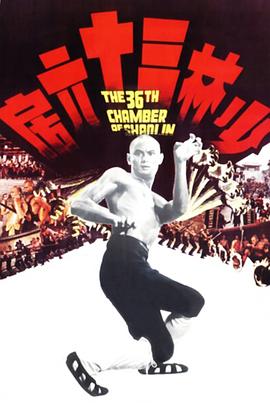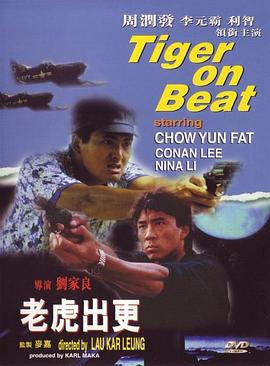剧情介绍
文|青砖
 "
" 编辑|青砖
一场关于“十八般武艺”的争论,毫无征兆地拉开序幕!南宋的翰林学士,手一挥,已在《翠微北征录》卷七将“军器三十有六、武艺一十有八”掰开揉碎,先后冷不丁地把弓推在第一位。大家都说这就是那所谓“十八般武艺”的祖籍,一传十,十传百,还真没几个人追溯过它的老底。即使是如今一查诸多文献,细节藏在水泊梁山、江湖戏班、各家谱牒里,真真假假,好像总有点儿分不清。
话说十八般武艺真的只有十八种?明明各类旧籍,将兵器列过一遍,枪、刀、剑、矛、弩、斧、棍,稀奇古怪的总不止这点。渐渐地,这“十八般”也像一种习惯。而真正打仗的人却压根儿糊涂,遇着危急,手边有啥用啥。
北宋熙宁元年,兵器的分等、技艺的考核,其标准一板一眼就在那里,弓、弩的力道细致区分。南宋还专门给弓箭手制定了考核要求:六十步,射八箭,至少命中五箭,这个比例还不算苛刻?兵器的分量就此具象化,人才的选拔也在重重标准里愈加严谨。
可在民间,“十八般武艺”更像个人人都晓得的名头。坊市里调皮的小儿唤作“只会白厮打”“哪会十八般武艺”,张口就能接,生活气息扑面而来。那些出身不高的武夫,世代靠艺谋生,练刀耍枪,无偿地为乡里效力,却常常受人忽视。
顺着这些支离破碎的记载,明清人再往里添油加醋。明代百回本《水浒传》一回合下来,把十八种兵器搬上舞台,史进练的无一不精,这种全能早已成了宋代好汉的标配。他们的身影在养兵场和坊巷间闪转腾挪,一把大刀能换半生安稳,一支长枪赢得凌厉声名。
细看“十八般武艺”的长短搭配,九长九短,刀、枪、棍、叉、钩、戟、锏、拐、杵。每多一本笔记,兵器的种类就水涨船高。有人总结得头头是道,有人写得云山雾罩,这仿佛就是古人对复杂世界的偷懒归纳。
宋人视弓为王。弓箭、步箭、袖箭,神臂弓横空出世,李宏一箭穿透三百余步之外,这夸张到底是真是假?《宋史》记得牢,数据也经得起琢磨,神臂弓身长三尺二,弦紧箭疾,最多射到三百七十来米。这个跨度,就算有人质疑,也无计可施,因为明初还在广泛装备,传承十数代未见减弱。
弩的功效更不提了。北宋“床弩”声名远扬,双弓床弩、合蝉弩、三弓弩,兵书里总要各点一下名。其实大弩的用法只在攻坚守城时才见,平时多半还是靠实用的小型弩,箭矢密集之下,列阵排布讲求精细。
宋军选拔弓弩手极严,步骑各有偏重,标准定得硬,挽弓三石以上为上档,重器非力壮者不能胜任。若说宋军重视武艺,一部分来自常年与辽金夏的攻伐压力,屡次战败中,意识到精细兵器和实操技艺才是战争本钱。可真到了性命攸关的时刻,再多的标准也成了摆设。毕竟,有几个士兵能做到百步穿杨?有本事的自然光宗耀祖,没有天赋的长年操练,也是徒然。
枪与矛,在战场上极是管用。结构千变万化,一柄枪上有时能挂倒钩、环子,或装上重头、小铁盘,变化首尾难断。宋人说“长兵以卫”,不是没有道理。大敌临门,阵前站好长枪队,拒马为军阵最外层,枪林矛阵才是盾墙之核心。那些挽强弓的人待在后头,兵书中未必都写明白,实战却时常演变,灵活得很。
韩琦规定:马上使枪,左右十刺,五中木人算及格。铁鞭、铁简、棍子、双剑、大斧,皆为配练,也讲究配合。还有岳飞、李全那样边境名将,枪法盛名传世,连队伍里夫妻档都拿出十八般本领,千金难买。
奇怪的是,有人觉得宋代长兵、短兵配比极讲究,每战以长枪居前,刀剑供补。可是在文献众多记号下,具体实战和排练总会有偏差,各地招募,自家习俗,杂糅之后产出一个四不像军种。
刀法粗犷霸道——单刀、双刀、斩马刀、屈刀等,招式多随地形、马步而变。大刀先劈后拦,强敌压阵时必须豁出去。单刀快准狠,双刀绵密灵动。宋代刀型多,长柄刀之所以盛行,很大一部分受外患刺激。辽、西夏、金、蒙古逼近,机动力和攻击力都成兵法要义,所以各种大刀应运而起。
剑不及刀猛,却历代身份最高。唐宋以降,舞剑表演风靡贵族。宋太宗选军中勇士舞剑,数百人轮番掷剑空中,自古“文人爱剑”,不完全是虚荣。后来,各地的武术流派,又赋予剑法不尽相同的变化和故事。
盾是攻防兵器之基,早在殷商周就有原始形制。宋军大盾进攻城池,牛皮蒙裹,坚不可摧,木盾铁盾服役多种场合。牌、棒与枪、杈成为最常出现在演阵、比赛、禁苑练将中的常见器物。可惜盾虽坚,却并不是绝对防御,也常有被破的记载,历史上并没有绝对,只有相对优势。
再往下说,斧、锏、鞭、链、挝之类,某种意义上已经分不清是兵器还是劳作工具,实际在实战里出现频率不一。斧来源可追溯至黄帝时期,到了宋朝主要用于破坏敌军盾牌。鞭和锏则因便于随身携带、近战威慑,成为骑兵的备选。锏、鞭、链甚至在少数民族兵器中使用较多,被宋军引入加以改进,这种武器转化往往和战场应变相关。
又比如飞叉。出处多模糊,只能追溯南宋将军张纯自创。玩法只有抡、飞、盘、投、抢、接、打击几种,变化万端。练这家伙的,早先多是南方人,北派武术里极少。学南人,是舍不得放弃实用武器的优越感?倒不像。
马步军士春秋大教,演练阵法,表演功夫,走马舞刀,飞枪揭柳,把家底亮给世人。东京城里花妆军士上阵开门夺桥,刀盾格斗,喊冲杀号角,场面喧腾,既是技艺比拼,也是军威威慑。一字长蛇阵,两两对垒,格斗制敌的技巧从不缺乏想象力。
宋军演武的场面,展现了宋朝兵器和武艺的复杂与兴盛。这种高度的兵备水平,在对抗强敌时显得尤为关键。北宋东京武艺表演,南宋禁中春教,武士比拼的不是空洞的表演,而是真实技能。这一点,现代很多武术流派其实难以比拟。你说练兵没用?实际对比辽金夏战斗力,宋军装备、条令、实训的精细化,毋庸置疑领先一头。
即便如此,宋兵常陷劣势,一部分并非技艺问题,而是将领指挥、士气与财政支撑的复合难题。装备再优、演练再强,若临阵退缩,谁肯说自己十八般武艺无敌江湖?这剖白下藏的失落,其实比技艺本身更让人唏嘘。
更有意思的是,二流武夫和英雄的差距,往往不是单一器械或者某一武艺。有的人值得一试,有的人只会虚张声势。练到极致或许百无禁忌,练到半路也许自我陶醉,自古皆然。总之,宋朝的武备故事,不止于“十八般武艺”的条条框框,也不止于将军名将的威风凛凛。真正彩色的,是无数兵器、无数练武人的荒唐、努力或狼狈。他们手里的刀枪剑戟里,藏着复杂人心,有投机、有执着,也有徘徊。
看似精致的一套武艺搭子,实际情况有时还不如一把普通锄头来得顺手。活在那个年代的宋人,谁知道自己明天会不会又遇上变化?标准的十八般武艺只是一种象征,兵器发展史里,不止有传说和光荣前人,更有纷杂琐碎的现实、没能流传下来的小发明,和被文人忽略的实践细节。到底哪一项才算真正的绝活,至今还未有人敢一口咬定。
所以,今天若说十八般武艺是宋武之魂,倒也不全对。毕竟每一本兵书里的刀枪都未必用得上一样,全会了也没人敢说打得赢敌人。局部的矛盾,历史的偶然,人物和兵器的误差,这一切,正好构成今日我们回望宋代武备的复杂面目。
有本事的人,用十八般武艺闯天下。没本事的,就算十八般都练,临阵还是发愣。这种状况,其实并不奇怪。宋人讲究细致又变通,条令和惯例时刻打架。现实里的技艺、武器、才智、胆气,有时候是各过各的桥,各守各的门。
归纳一句:“十八般武艺”,最终成了中国冷兵器史上一道不会消失也没法完满重现的风景。这风景,你要说它辉煌也好,说它稀松也罢,都不过如此。
——
数据、文献佐证:
《翠微北征录》《水浒传》《五杂俎》《坚瓠集》《梦溪笔谈》《宋史》《武经总要》《中国冷兵器史》(沈卫荣),结合中国知网与国家图书馆近年公开修订成果,以上细节数据与案例均可查证。
2024年互联网相关历史冷兵器研究、中文维基、微博科普及中华武术联盟权威发布为交叉背景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