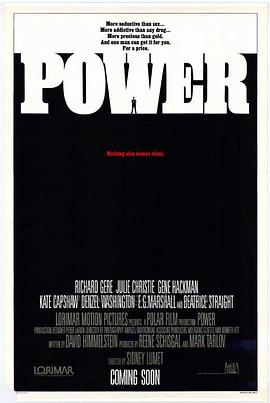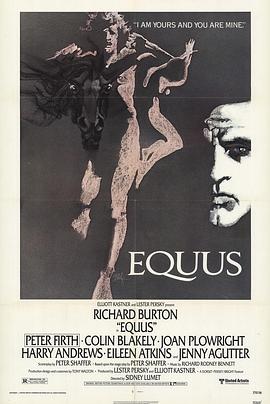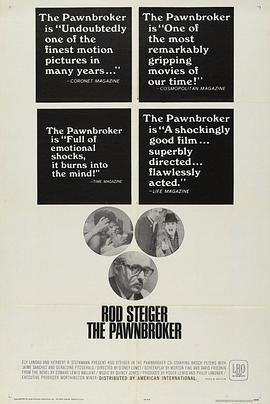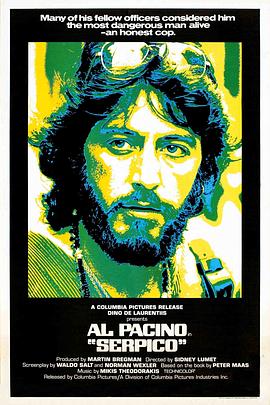剧情介绍
本文作者“虫二”,欢迎去豆瓣app关注ta。
“永远醉倒吧。那是唯一的问题,别的一切无关紧要。假使你不愿感觉光阴可怕的重担压在你肩头上,把你压倒在地上不能翻身,那么还是不断地醉倒吧。
用什么来醉倒?用酒、用诗、用仁义道德,什么都成,只要醉倒。”
——尤金·奥尼尔
瑞典皇家学院.《长夜漫漫路迢迢》首演.纽约科特剧院.1956
1956年首演节目单
奥尼尔的剧本与传统的“美国式”文学作品保持了距离,无论是他心目中理想的“新伦敦”,还是剧本中那股海与雾的气味。这样看来奥尼尔竭力将目的与思想变现的创作目的,似乎有了些反投机主义的倾向,二十世纪的美国文学里对于家庭的讨论远远低于个人,作家们强调社会问题是内心问题的映射,用流浪、用酗酒与性爱来试图唤起某种没有具体名状的精神。奥尼尔前期作品中也有类似的创作意向——《送冰的人来了》里那场群体性孤独式的狂欢。
在被普林斯端大学劝退、洪都拉斯淘金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水手生活之后,奥尼尔开始创作,写出关于欲望、宗教等题材的戏剧,作为美国戏剧中为数不多的“执剑者”,他可以说是较为完整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作为最后一部上映的戏剧剧本《长夜漫漫路迢迢》中这位“执剑者”最后抛出的问题——家庭和艺术的目的是什么——显得温情而计较。
据奥尼尔自述:“这是一部消除旧恨,用血与泪写的戏。”二十世纪文学中绝不缺乏自传式创作,多数以小说为主。《长夜漫漫路迢迢》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剧本的形式,以及据传基本没有改动的赤裸事实。作为自传性作品,这部四幕剧本只截选了冲突最为密集的时间段;而作为一部剧本,它又显得过于“冗长”,过于使人产生精疲力竭的负担感,尽管这种“精疲力竭”也是作者的功力所在。
它长得有些出奇了,以一种沉重严肃得黏稠滞重的语调,直接地把读者,或者说是观者反复地牵引进那些回忆,和那间因父亲吝啬开灯而混浊阴暗的屋子,翻来覆去的语调,大声念着莎士比亚和波德莱尔的诗句,幽灵一样游荡的瘾君子母亲,放荡的长子,阴郁柔弱患痨病的次子。读者知道这是一部戏剧,而它在阅读过程竟里变成这等篇幅和气质。
电影改编海报
电影改编海报
《星期六评论》的henry hewes 在探讨此剧的普遍意义时,曾将人的生活分为几个不同的阶层:有时,生活在“冲动”的阶层上,即对食物做不假思索的直觉反应;有时,生活在“社会”的阶层上,装模作样地去应付,甚至欺骗别人;有时“妥协”,对一切因循苟且;有时“自省”,向内心搜寻真理;再有时,生活却在“逃避”与“幻觉”中。他说在《长夜漫漫路迢迢》中,奥尼尔将自己,哥哥与父母表现得在这几个阶层上此起彼落、跳着人生的魔舞。
奥尼尔妻子卡洛泰表示奥尼尔在创作这部戏剧时极为辛苦,试图抓住记忆里真实的一切,但他做不到具体。这样雄心勃勃地计划着描述那过去的“破碎之家”,他就必须重返到“毒瘾”、“贫穷”、“荒废”“放荡者”这样的语词之间,这痛苦来自于奥尼尔执意要通过写作来缓解,执意要说出真相从而原谅过去。在“表现”这个戏剧创作的核心观念里,行动不再是为了改造生活,同样也可以使逃避生活,如果想要赋予这种逃避一个意义,就必须理解逃避。
也许有时候,在宫殿的楼梯上,在沟渠彼岸的绿草地上,活在你自己孤寂、沉闷的斗室中,你会醒来发觉醉意已经半消或是全退。那么就去问,问风、问浪、问天上的星星和飞鸟、问时钟,问一切能飞、能叹、能摇摆和歌唱的、能说能讲的,问它是什么时辰了。那么,风、浪、星星、飞鸟、时钟会告诉你:“是醉倒的时辰了!醉倒吧,假使不愿做光阴的奴隶和牺牲者,不断地醉倒吧!用酒、用诗、用仁义道德,什么都成。”
奥尼尔与卡洛泰
在《长夜漫漫路迢迢》里,奥尼尔找到了他的最终题材——家庭,实际上他也从未远离这一题材,这是理解奥尼尔的一本关键之作,他最后一击般的开拓。桑塔格在《反对阐释》里提到:一种新形式的说教占据诸类艺术,它的确是艺术中的“现代”因素。其核心信条是这一种观念,即艺术必须发展。其成果是这一类作品,其主旨是要推动体裁的历史,在技巧上开拓创新。
戏剧作为自古典主义时期之始即欣然发展的文类,前有莎翁莫里哀契诃夫之光洁璀璨,后有米勒贝克特等人,剧本形式的写作已经严格规定了体裁,如何在既定题材内再次发挥“现代”因素,贝克特的散体作品的要旨是展示词法、标点法、句法和叙述秩序如何能够被重新调整,以表达意识的连续的出窍状态。而剧本作为戏剧台词和念白显然在文字的结构性功能上略有无力,它必须是整体一致的,连贯和谐的,几乎可以说的是,它比其他文类更需要注重观者感受。
《长夜漫漫路迢迢》里,奥尼尔使戏剧发生在故事已经发展一段时间之后,那时间是清晨早饭过后,父亲蒂龙已经在同一部戏剧上荒废了自己的表演天赋,整日里专注于如何节省金钱避免走向“穷人院”的命运;母亲玛丽因为伴随丈夫常年奔波表演的寂寞,以及那个曾经夭折的幼子转而向毒品寻找安慰;长子杰米沉迷酒精与妓女,被大学劝退在家中无所事事;小儿子埃德蒙已经出现痨病的早期症状。
电影截图
这些信息随着角色对话逐渐显形。不断地制造疑问,不断地给予信息,奥尼尔看起来放弃了浅显易懂的叙事顺序和老旧的美学理论,这样的做法一旦失去足够严肃的内核,势必导致大量的既乏味又做作的作品。或许人们曾经期盼那种古老的文学活动方式,那些非自我意识,那些大段大段华彩横溢的念白。然而奥尼尔这样克制且真诚、强迫读者接受“现代”这个略显拙劣时期的戏剧家,必定会使读者看到这种转变的必然性。尽管这个过程已经比我们预想的要慢上许多了。
在失去米勒与奥尼尔之后,美国的戏剧界所展示出的前景说得上是凄凉,但作为一种文学形式,戏剧从未能够在现代艺术革命中置身事外,趣味性也越来越显示出复杂和严肃。奥尼尔的反现实主义的理由看起来着实令人信服,现实并非是一清二楚的,它的常态更像是在他的诸多剧本中氤氲的海与雾气。
那些大多数作品中的逼真性和它所引起的那种不假思索的对于生活的论断,对号入座的真实感,是应该令人怀疑的,怀疑也是我们时代的特性。生活不是栩栩如生的,一个故事也未必在最后选择开放式结尾或者闭合式的高潮结尾,它无疑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结局和去向,而我们似乎也不需要一个结局来当做安慰。
“什么都不长久,
眼泪和欢笑,
爱和欲和恨:
我们的躯壳都不再包含,
一过了鬼门关,
什么都不长久,
酒和玫瑰的日子:
从朦胧的幻梦中,
我们的路程一出现,
又消逝在幻梦中。”
尤金·奥尼尔
“新伦敦”奥尼尔大街
瑞典皇家剧院改编《命运之路》.2017
瑞典皇家剧院改编《命运之路》.2017
注:题目与文中引用皆出自尤金·奥尼尔 著 乔志高 译《长夜漫漫路迢迢》;
参考书籍:约翰·盖尼尔《奥尼尔及其作品》、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尤金·奥尼尔《一点诗人气质》;维基百科 尤金奥尼尔 条目;
图片来自网络。
(全文完)
本文作者“虫二”,现居pai,目前已发表了121篇原创文字,至今活跃在豆瓣社区。下载豆瓣app搜索用户“虫二”关注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