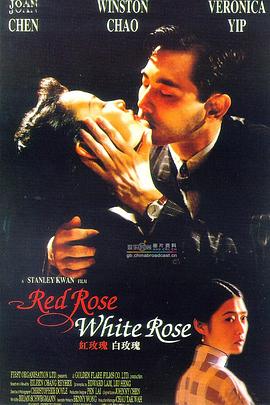剧情介绍
二战胜利七十周年,欧美影坛关于二战历史的片子也骤然增多。在这个更加个人的时代,影片也将更习惯于用个人史,讲述家国史,用情感审判情感,用道德重新找回道德。影片《金衣女人》,是近期此类作品中质素尚可的一部。
在目前的欧洲,许多二战题材影片不再侧重于审判罪恶的轴心国或者简单重现当年的惨烈。更多电影人把关注点放在了欧洲“反犹主义”,以及平凡人对恶的不识别,乃至盲从、欢欣鼓舞。这种反思在今日弥足珍贵:简化式地批判德国纳粹,很容易让人们忽略纳粹产生、日渐壮大的土壤,仿佛他们当年横空出世。更多的电影在提示人们,最终雪崩发生时,从没有一片雪花会认为是自己的责任。
玛利亚的犹太家族非常富有,她结婚时,“半个奥地利的艺术名流”都来了。而在她和丈夫逃向机场的生死之路,十个奥地利人只有两三个帮他们遮掩,其余的都毫不犹豫地报警,或者给纳粹警察指认他们逃亡的小巷。1941年的维也纳,群情激奋,犹太人的富裕和原罪,成为任何人可以审判任何人的鞭柄。跪在街口的犹太家庭用强酸清洗着路面,万众欢呼声中,是历史的寒意,人心的寒战。
艺术之都维也纳,金碧辉煌又绿意明灿。而这里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犹太人聚居地之一。20世纪初,这里不断酝酿的“反犹”政治与希特勒互相作用。在纳粹统治前,“反犹”早已成为奥地利各地选举的最佳得分点。玛利亚抛下了已被软禁的父母,逃到美国。她封存记忆,成为一个孤僻执拗的老太太。影片正是通过慢慢启动她的情感,启动她最深处的愤怒和对父母的悔恨,在寻画、要画的过程中,完成一个人的独白,完成与一段大历史的正面对视。
画作《金衣女人》是艺术家克里姆特的作品,描绘了玛利亚的叔母,倾城的名美人。纳粹瞠目于其美却不喜欢美人是个犹太人的身份,强取豪夺之后,整个奥地利合力把这个标签轻轻抹去,画作名字也从《阿黛尔·布洛赫·鲍尔夫人》变成了《金衣女人》,成为奥地利版蒙娜丽莎。战后,奥地利国家博物馆拥有了这幅名画——“她”,成为奥地利的象征之一。
金箔簇拥的光影里,美人似笑非笑的容颜并不快乐。整个奥地利为之着迷,不愿归还——不还,实际上就是一种对于历史的回避。这里面藏着一系列的问题,你承认了一个,就会承认一个巨大的系列。奥地利不想,而时至今日的大多数国民,也不想。
与玛利亚周旋的奥地利,浓缩为一个面目模糊的官僚系统,僵硬、虚伪、逃避。所有无法从深处真正内省的人,和当年助纣为虐的人,似乎就是同一拨人。每个人“贡献”的力量并不大,但足够让错误变得正常而不觉察。
在奥地利,类似情况的艺术珍品成千上万。政府怕开这个口子,又想表明自己反省二战的国际形象,也因此,电影最大的悬念一直上上下下,角力感十足。作为一个英美合拍片,这种无名小卒搬倒一头象的反转驾轻就熟。玛利亚势单力薄,但胜在人心——即使最后的审判在奥地利法庭而非美国法庭进行,“陪审团”依然忍痛割爱,按照道德和法律,把国家珍宝还给了当年备受摧残的人。不具名的陪审团,并未浓墨重彩的法庭戏,在双方都竭力的最后,用小手指轻轻一推。
整部片子简单流畅,是一个复述真实故事的过程。也因为简单流畅,戏剧张力和能够刺进人心的那一下都变得松垮。它像一种非常优雅的痛苦,非常优雅的去抗争,带给人们隔岸观澜的平顺。影片想表达的东西也有点太多,比如帮助玛利亚诉讼的律师,从不关心祖先如何流亡到美国,到立于大屠杀纪念碑前深深痛哭,到辞职豁上一切和一个国家拼上……并行的这条线,一直在表达一种对于做一件“对的”事情的赞许,整个过程就是一种净化。但它不断干扰着主线的节奏,显得重点模糊。
不过对于这样的影片,不愿意太挑剔。它从个人而来,穿越整个家国历史,然后回归个人。舍弃娱乐属性,它提供的信息和视角本身,已经具备了相当的价值。好电影也许还算不上,但它的的确确有好的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