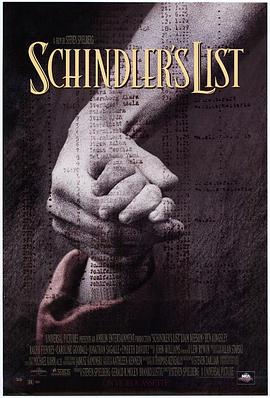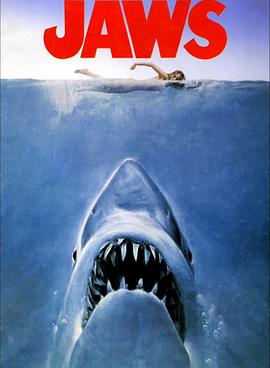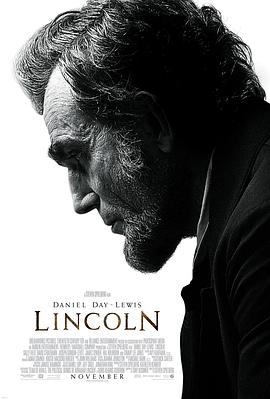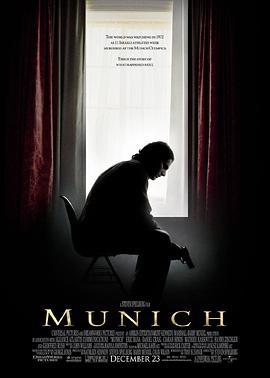剧情介绍
上周末,经朋友介绍,我有幸参加了苏州工业园区电影协会组织的观影活动,看了斯皮尔伯格1987年的大片《太阳帝国》。影片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少年吉姆是上海某英国富商的儿子,生活舒适,对零式战斗机非常崇拜,做梦都想成为一名飞行员。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吉姆和父母失散,被送进了集中营。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向锦衣玉食的他竟很快适应了那里的环境,甚至比不少成年人混得还好。就这样,伴着隔壁军事基地里的飞机起落,吉姆度过了集中营里异常艰苦的三年时光,并最终与父母在战后重逢。
纵观全片,两个半小时总体来说起伏不大,有些耐不住性子的我甚至还曾在中间几度看表。在观影结束后的交流环节中,一位会员坦承他睡着了。我虽然没有犯困,但心情也确实没有产生太大的波澜。然而我毕竟是要就此写点东西的——作为加入影协的“投名状”,一篇影评(或者更恰当一点,观后感)是我给自己定下的任务。鉴于大片总是有很多解读的空间,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非常重要,我思前想后,决定另辟蹊径谈谈里面的教育问题。
“穷养儿,富养女”是中国流传甚广的一条古训。在没有进入集中营之前,吉姆所接受的,应该是不折不扣的富养——住着带有游池、草坪的豪华洋房,坐着logo别致的packard豪车,出门有司机接送,饮食有老妈子照顾,出入的都是高档派对,结交的皆为富商名流,曾受过宋庆龄的接见说明他所处的绝对是上流社会,和美国水手贝希初次打交道时的幼稚表明他显然不了解民间疾苦。
然而自从在逃难的人流中为拾起玩具飞机而撒开母亲手的那一刻,这些好日子就宣告结束了。从此,小吉姆迎来了颠沛流离的艰苦岁月,成了一个事实上的、无依无靠的孤儿。在集中营里,他眉头都不皱一下地吞下米粒里夹杂的象鼻虫,身上穿着的也是非常不合身的成人外衣。“为了吃饭什么事都能干”,这条集中营真理他很快就学会了,并且在实践中运用得驾轻就熟。可以说,如果把“穷养”的那个“穷”字仅仅局限于物质,那么彼时的他可谓是被“穷养”到了极致,尽管“养”他的并非自己的父母,而是一群凶神恶煞的日本兵。
一前一后,一富一穷,在成长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无疑都会对吉姆的未来产生影响。在富养的阶段,他初步养成了绅士的风度和品格,见惯了大场面,也锻炼了自信心;在穷养的阶段,他学会了在逆境中不悲观、不绝望,能平静接受苦难的磨练,积极应变,主动作为。当集中营的成年难友称赞他“越来越像你父亲”的时候,他在富养阶段被教导的乐于助人的美德依然还在;被贝希利用继而背叛的经历则为他补上了人生的重要一课,明白了千万不可以轻信于人。
据我设想,在经历过鲁滨逊重返文明世界似的短暂不适之后,和父母团聚后的小吉姆一定会如虎添翼、活得更好。毕竟,他已然接受过逆境的洗礼,完成了残酷的“挫折教育”。尽管影片声称“根据真实经历改编”,但吉姆不但没有沦落为一个小流氓,相反倒让美德愈发闪光的故事,还是美得如同童话。这段可怕的际遇按说不可能不留下些许阴影,但至少电影里流露不多。
在影片的开头部分,吉姆曾在晚上偷吃东西被保姆劝阻时很不客气地训斥了她。而等到此人趁乱偷东西遭到制止时,又回头扇了他一记耳光作为报复。作者(无论是原著作者还是电影编剧)的种族歧视倾向让片中没有一个值得尊敬的中国人形象,而吉姆那彬彬有礼的绅士范儿,显然也不适用于底层的华人。
除却在中国人面前的傲慢,吉姆总体上应该算得上是一个好孩子。这既要归功于他的亲生父母,也要感谢在集中营里给他抚慰和关照的维克多夫人、罗林斯医生。穷养和富养其实并非仅仅体现为生活条件的好赖——没钱固然谈不上富养,但物质需求的满足或压抑只是一种手段,提高精神境界才是教育的目的之一。
而这些,就是我对《太阳帝国》的另类感想。它可能有点儿跑偏,但总好过老生常谈、拾人牙慧吧?
砖已抛出,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敬待诸位的那方美玉!
韩冷
2016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