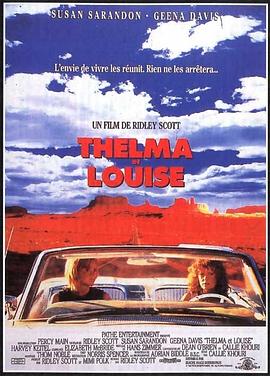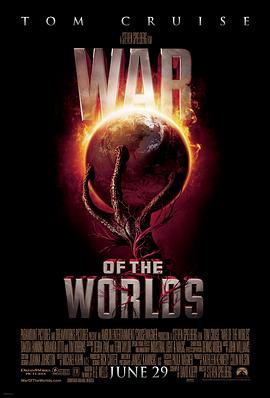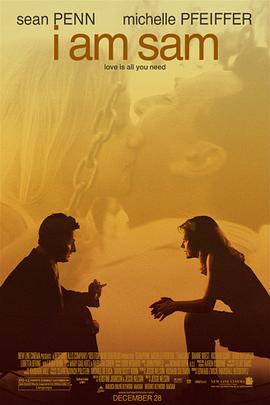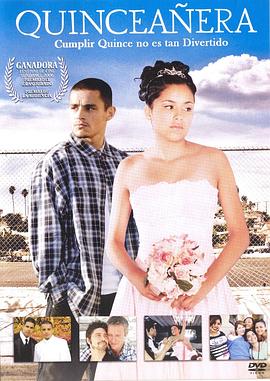剧情介绍
《《最后的罗宾汉》:一场被时代默许的禁忌之恋,还是母女共谋的欲望陷阱?
2013年上映的传记剧情片《最后的罗宾汉》(The Last of Robin Hood)以好莱坞黄金时代的传奇影星埃洛尔·弗林(Errol Flynn)生命最后两年为蓝本,揭开了一段震惊1950年代美国社会的丑闻:58岁的银幕“罗宾汉”与17岁少女贝弗莉·林恩(Beverly Aadland)之间长达两年的隐秘恋情。更令人瞠目的是,这段关系并非秘密——贝弗莉的母亲弗洛伦斯不仅知情,还主动促成、全程参与,甚至在弗林临终时默许女儿守在其病榻旁。
影片由理查德·格雷泽与沃什·韦斯特摩兰联合执导,凯文·克莱恩饰演风流不羁却日渐衰朽的弗林,达科塔·范宁化身天真又早熟的贝弗莉,而苏珊·萨兰登则精准刻画了那位复杂到令人不安的母亲弗洛伦斯。三人构成的三角关系,远非简单的“老少恋”可概括,而是一场关于权力、操控、幻想与自我毁灭的精密共舞。
故事始于1959年10月,弗林猝然离世,死于心脏病发作,怀中正是年仅17岁的贝弗莉。这一爆炸性新闻迅速引爆舆论,但影片并未止步于猎奇,而是通过弗洛伦斯面对记者的回忆式叙述,层层剥开这段关系背后的真相。弗洛伦斯曾是过气的舞蹈演员,一生渴望重返聚光灯下。当她发现女儿贝弗莉拥有成为明星的潜质后,便将全部野心投射其上。恰在此时,弗林出现了——这位昔日银幕英雄虽已酗酒成性、事业滑坡,却仍保有某种危险的魅力与残存的行业影响力。
弗洛伦斯没有阻止,反而主动安排女儿与弗林“约会”,从最初的试镜机会,到后来的欧洲旅行、同居生活,她始终以“监护人”身份合理化一切。影片最令人心寒的细节在于:弗洛伦斯并非被迫沉默的旁观者,而是积极的共谋者。她替女儿伪造年龄证明,对外宣称贝弗莉已满18岁;她在弗林家中安顿下来,以“助理”身份监视并维系这段关系;甚至在弗林健康急剧恶化时,仍坚持让女儿留在他身边,只因她相信这是贝弗莉通往星途的唯一跳板。
而贝弗莉呢?达科塔·范宁的表演微妙地呈现了一个被母亲洗脑、又被明星光环迷惑的少女心理。她对弗林的感情混杂着崇拜、依赖、恐惧与一丝真实的依恋。她以为自己在谈一场浪漫的恋爱,实则早已沦为母亲野心与弗林暮年虚荣的双重祭品。影片多次展现她在镜子前模仿玛丽莲·梦露,暗示她对“明星身份”的执念并非源于热爱表演,而是对符号化成功的盲目追逐。
至于弗林,凯文·克莱恩赋予这个角色一种悲凉的颓废感。他不再是那个挥剑跃马的侠盗罗宾汉,而是一个被酒精侵蚀、被时代抛弃的男人。他需要贝弗莉的青春来确认自己尚未老去,也需要她的顺从来填补内心的空洞。他清楚这段关系的荒谬,却无力挣脱——既无法抵抗诱惑,也无法承担后果。他的死亡,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解脱,也是这场畸形关系必然的终点。
《最后的罗宾汉》之所以未能成为爆款,并非因其题材不够劲爆,而恰恰在于它拒绝煽情与道德审判。导演以冷静近乎疏离的镜头,呈现一个没有英雄、也没有纯粹受害者的故事。弗洛伦斯不是恶魔,她是被父权娱乐工业异化的母亲;贝弗莉不是无辜羔羊,她是被灌输错误价值观的共犯;弗林更不是反派,他是旧好莱坞神话崩塌后的残骸。
影片的真正批判对象,是那个默许甚至鼓励此类关系的时代结构。1950年代的好莱坞,年幼女星被“发掘”、被“培养”、被“拥有”是公开的秘密。制片厂制度下的女性,尤其是未成年女孩,往往被视为可交易的资产。弗洛伦斯的行为固然极端,但她的逻辑却深深植根于那个系统的规则之中——用身体换机会,用青春换资源,只要能成功,手段无关紧要。
今天回看《最后的罗宾汉》,其现实意义愈发尖锐。在MeToo运动席卷全球之后,我们才真正意识到,像贝弗莉这样的故事并非孤例,而是系统性剥削的冰山一角。影片结尾,弗洛伦斯面对记者质问时那句轻描淡写的“我只是想让她成功”,道出了多少“为你好”背后的控制与自私。
这或许就是《最后的罗宾汉》最令人不安之处:它讲述的不是一个遥远的丑闻,而是一面照向现实的镜子——当梦想被包装成牺牲,当爱被置换为利用,谁又能说自己从未在某个时刻,成为过弗洛伦斯、贝弗莉,或那个垂死的罗宾汉?
2013年上映的传记剧情片《最后的罗宾汉》(The Last of Robin Hood)以好莱坞黄金时代的传奇影星埃洛尔·弗林(Errol Flynn)生命最后两年为蓝本,揭开了一段震惊1950年代美国社会的丑闻:58岁的银幕“罗宾汉”与17岁少女贝弗莉·林恩(Beverly Aadland)之间长达两年的隐秘恋情。更令人瞠目的是,这段关系并非秘密——贝弗莉的母亲弗洛伦斯不仅知情,还主动促成、全程参与,甚至在弗林临终时默许女儿守在其病榻旁。
影片由理查德·格雷泽与沃什·韦斯特摩兰联合执导,凯文·克莱恩饰演风流不羁却日渐衰朽的弗林,达科塔·范宁化身天真又早熟的贝弗莉,而苏珊·萨兰登则精准刻画了那位复杂到令人不安的母亲弗洛伦斯。三人构成的三角关系,远非简单的“老少恋”可概括,而是一场关于权力、操控、幻想与自我毁灭的精密共舞。
故事始于1959年10月,弗林猝然离世,死于心脏病发作,怀中正是年仅17岁的贝弗莉。这一爆炸性新闻迅速引爆舆论,但影片并未止步于猎奇,而是通过弗洛伦斯面对记者的回忆式叙述,层层剥开这段关系背后的真相。弗洛伦斯曾是过气的舞蹈演员,一生渴望重返聚光灯下。当她发现女儿贝弗莉拥有成为明星的潜质后,便将全部野心投射其上。恰在此时,弗林出现了——这位昔日银幕英雄虽已酗酒成性、事业滑坡,却仍保有某种危险的魅力与残存的行业影响力。
弗洛伦斯没有阻止,反而主动安排女儿与弗林“约会”,从最初的试镜机会,到后来的欧洲旅行、同居生活,她始终以“监护人”身份合理化一切。影片最令人心寒的细节在于:弗洛伦斯并非被迫沉默的旁观者,而是积极的共谋者。她替女儿伪造年龄证明,对外宣称贝弗莉已满18岁;她在弗林家中安顿下来,以“助理”身份监视并维系这段关系;甚至在弗林健康急剧恶化时,仍坚持让女儿留在他身边,只因她相信这是贝弗莉通往星途的唯一跳板。
而贝弗莉呢?达科塔·范宁的表演微妙地呈现了一个被母亲洗脑、又被明星光环迷惑的少女心理。她对弗林的感情混杂着崇拜、依赖、恐惧与一丝真实的依恋。她以为自己在谈一场浪漫的恋爱,实则早已沦为母亲野心与弗林暮年虚荣的双重祭品。影片多次展现她在镜子前模仿玛丽莲·梦露,暗示她对“明星身份”的执念并非源于热爱表演,而是对符号化成功的盲目追逐。
至于弗林,凯文·克莱恩赋予这个角色一种悲凉的颓废感。他不再是那个挥剑跃马的侠盗罗宾汉,而是一个被酒精侵蚀、被时代抛弃的男人。他需要贝弗莉的青春来确认自己尚未老去,也需要她的顺从来填补内心的空洞。他清楚这段关系的荒谬,却无力挣脱——既无法抵抗诱惑,也无法承担后果。他的死亡,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解脱,也是这场畸形关系必然的终点。
《最后的罗宾汉》之所以未能成为爆款,并非因其题材不够劲爆,而恰恰在于它拒绝煽情与道德审判。导演以冷静近乎疏离的镜头,呈现一个没有英雄、也没有纯粹受害者的故事。弗洛伦斯不是恶魔,她是被父权娱乐工业异化的母亲;贝弗莉不是无辜羔羊,她是被灌输错误价值观的共犯;弗林更不是反派,他是旧好莱坞神话崩塌后的残骸。
影片的真正批判对象,是那个默许甚至鼓励此类关系的时代结构。1950年代的好莱坞,年幼女星被“发掘”、被“培养”、被“拥有”是公开的秘密。制片厂制度下的女性,尤其是未成年女孩,往往被视为可交易的资产。弗洛伦斯的行为固然极端,但她的逻辑却深深植根于那个系统的规则之中——用身体换机会,用青春换资源,只要能成功,手段无关紧要。
今天回看《最后的罗宾汉》,其现实意义愈发尖锐。在MeToo运动席卷全球之后,我们才真正意识到,像贝弗莉这样的故事并非孤例,而是系统性剥削的冰山一角。影片结尾,弗洛伦斯面对记者质问时那句轻描淡写的“我只是想让她成功”,道出了多少“为你好”背后的控制与自私。
这或许就是《最后的罗宾汉》最令人不安之处:它讲述的不是一个遥远的丑闻,而是一面照向现实的镜子——当梦想被包装成牺牲,当爱被置换为利用,谁又能说自己从未在某个时刻,成为过弗洛伦斯、贝弗莉,或那个垂死的罗宾汉?
猜你喜欢
影片评论
评论加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