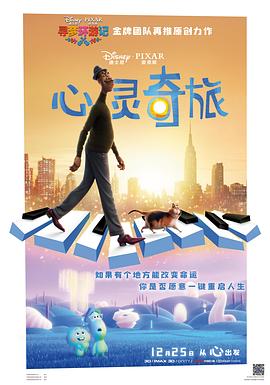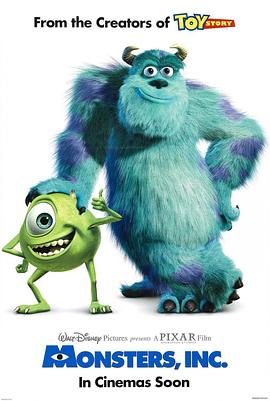剧情介绍
《头脑特工队》讲述孩子心理成长的奥秘
第一篇
打开脑洞来一场旅行吧!
——《头脑特工队》的科学观影姿势 作者:小泡
一个名叫riley的小女孩跟着父母跨越大半个国家从明尼苏达搬到了旧金山,面对着新环境的全面挑战,然而这只是故事的背景。真正的故事存在于她的大脑内:在头脑的“司令部”里住着五位情绪小人,他们一同操纵着riley的行为,管理司令部外神奇的长期记忆、潜意识……
这是一个有科学理论支撑,却又完全虚构的世界。据说电影起源于导演道格特的一个真实的困惑:自己十岁刚刚出头的女儿经历了和电影主人公类似的转变,“她开始变得越来越安静,越来越内向。老实说,这种情况在我自己心里引起了很大的不安和恐惧;它也让我开始好奇,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脑海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于是,导演和电影制作团队开始研究起大脑的运转方式。他们还和以研究情感闻名的心理学家保罗·艾克曼(paul ekman)以及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达契尔·克特纳(dacher keltner)一起讨论过电影背后的心理学原理。
看看这个关于“头脑”的精彩故事吧!你不仅可以潜入了人体最神秘的器官展开一段天马行空却又逻辑自洽的大脑之旅,也许还可以重新认识自己的记忆、情绪和人格的来龙去脉,或者以一种新的视角来回顾自己走过的成长之路。
当五个情绪小人操控了你的大脑
在riley的大脑中,有五个闹腾活跃而又各司其职的情绪小人:“快乐”(joy)、“悲伤”(sadness)、“恐惧”(fear)、“厌恶”(disgust)和“愤怒”(anger),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了情绪如何掌控了我们的行动,以及与周围人的互动方式。
为什么选这些情绪做主角?其实心理学家早就提出了人类究竟具有多少种基本情绪的问题。通过在不同文化群体中进行面孔表情识别的研究,心理学家paul ekman认为人类存在6种基本情绪:愤怒、厌恶、恐惧、快乐、悲伤、惊讶,所有人都能够理解和辨认这些情绪。据说导演舍弃了“惊讶”这种情绪角色,是因为觉得它和“恐惧”比较相似。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种情绪在生活中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快乐”是那个总想逗你开心的角色,总是精力充沛上蹿下跳,遇到困难时的口头禅是“我能搞定”,让你充满坚持下去和扭转困境的勇气。“愤怒”是当你受到不公平对待时的反应方式,如果当一些行为对你产生了直接威胁,防御或攻击也许是解决危险的最迅速的方式。“害怕”是提醒你远离危险的角色,试想当你在丛林中遭遇凶猛的黑熊,如果你还有胆去人家跟前大摇大摆地走一遭,恐怕早已性命不保。“厌恶”并没有什么卵用?才不是呢!它会让你远离疾病,抵御有害物质入侵,想想大部分让你觉得恶心的都是什么……
对了还有“悲伤”,这个角色一开始似乎挺让人嫌弃,衣着臃肿行动迟缓,总是悄无声息地给主人制造麻烦,让riley在新同学和老师面前出丑,让美好的记忆染上忧郁的色彩…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种情绪在生活中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快乐”是那个总想逗你开心的角色,总是精力充沛上蹿下跳,遇到困难时的口头禅是“我能搞定”,让你充满坚持下去和扭转困境的勇气。“愤怒”是当你受到不公平对待时的反应方式,如果当一些行为对你产生了直接威胁,防御或攻击也许是解决危险的最迅速的方式。“害怕”是提醒你远离危险的角色,试想当你在丛林中遭遇凶猛的黑熊,如果你还有胆去人家跟前大摇大摆地走一遭,恐怕早已性命不保。“厌恶”并没有什么卵用?才不是呢!它会让你远离疾病,抵御有害物质入侵,想想大部分让你觉得恶心的都是什么……
对了还有“悲伤”,这个角色一开始似乎挺让人嫌弃,衣着臃肿行动迟缓,总是悄无声息地给主人制造麻烦,让riley在新同学和老师面前出丑,让美好的记忆染上忧郁的色彩…
心理学家伊扎德(izard)的情绪分化理论认为,悲伤情绪对人们具有重要的生存和适应价值。当悲伤发生时,人们可能由于体验到悲伤而激发改善自己处境的愿望并优先考虑重要的目标和角色,以重新达到生活的平衡。比如在经历一个无法挽回的丧失之后,个体可能要评估丧失程度及其对未来生活的影响,重新确立自己的目标和角色。
悲伤也有重要的社会功能:悲伤发生时,个体感受到缺乏自我掌控,于是产生了求助于社会网络中其他人的需要。所以悲伤可能让个体向他人发出求助信息,加强社会联系。
就像影片的最后,差点离家出走的riley面对父母,诉说着自己的悲伤,自己对新环境的不适应,得到了父母的理解与共情,一家人达成和解,让一座“家庭岛”重新拔地而起。反映了接纳并且表达这样一种负性情绪的重要性,快乐会有失灵的时候,悲伤也能成为扭转局面的关键角色!
找回“记忆球”的探险之旅
电影把抽象的记忆具象化成了许许多多发光的玻璃球,它们被区分为短期记忆、长期记忆和核心记忆等不同类型,在大脑中有各自的存放区域。在riley睡觉的时候,白天产生的记忆球(短期记忆)就会滚过一系列的斜坡和管道,进入层层叠叠宛如迷宫的长期记忆的区域。科学研究也证明了,睡眠确实能够促进大脑中长时记忆的巩固。而这些长时记忆区中的记忆球有的已经褪色得非常严重了,而且对生活实践基本没有指导作用,它们就被头脑工人(mind worker)们清理打扫,甚至被扔进像是深渊的垃圾堆的记忆废墟(memory dump)中,比如隔壁王叔叔家的电话号码,让你永远都想不起来了,也就是记忆遗忘的过程。
影片中的一个重要情节是:
riley的几个核心记忆球意外被吸进管道,与“快乐”和“悲伤”一道被送到了远离司令部的大脑深处。这些核心记忆球原本连接并点亮了,决定riley人格特征的几座岛屿--“冰球岛”、“淘气岛”、“友谊岛”和“家庭岛”。在核心记忆球丢失之后,这些人格岛屿一座座地倒塌,也引起了riley行为表现上的很大变化。riley的核心记忆,包括了温暖的家庭生活,一起玩耍的挚友,第一次爱上冰球,比赛拿了冠军等等,都是对过去特定情境中有关自我信息的回忆,这种与自我经历有关的记忆称为自传体记忆。
心理学研究发现,大多数人对于3岁之前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很难回忆起来,这种早期的记忆缺失现象,现在一般认为是由于孩子早期缺乏熟练的语言能力和稳固的自我概念。自传体记忆在学前期出现,父母的引导往往在孩子自传体记忆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比如帮助孩子把经历组织成能够叙述的故事,帮助他们去回忆对个人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自传体记忆开始可能只是“普通”或日常的情节记忆,比如昨天早餐吃了什么;但如果得到进一步加工,这些记忆才会成为被记住的个人生活经验的一部分。能够成为自传体记忆的事件,通常是那些对后继事件仍然具有意义的事件,而那些不太重要的事件,依照有机体“节约”的适应机制,自然地被我们遗忘了。
这种记忆到底对我们有多重要?心理学家james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人关于自我的记忆全部丧失的话,从本质上讲他此时已经成为了另外一个不同的人。自我与人格的同一性正是建立在记忆的同一性的基础之上,唯其如此,人才能成为完整的人。正如cohen (1989)所说:“我们的身份认同感与我们能否回忆起个人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那些不能回忆起个人生活事件的个体(如中风患者)会完全失去对自己身份的认识”。所以,自传体记忆为自我与人格的建构提供了基础。
然
而记忆并不是对现实世界的精确复制,我们在回忆时往往对记忆进行了重新建构。回忆以我们的心理环境为背景,这种心理环境既包含对当下作为刺激的外界事物的体验,也包含一些内部的心理因素比如动机、情绪、目标等等。这些因素可以会修改我们的记忆,带来我们毫无觉察的影响。比如当你在情绪低落时,回想起曾经与好友一起的欢愉时光,也不免笼上了一层冷色调的伤感。
看完这些,你是否不禁感叹,自己的思维活动、情绪反应的源头,竟如此奇妙!其实同样传奇的故事,每时每刻都在我们每个人的大脑中上演。如果你愿意,可以闭上眼睛想象一下,自己脑中的情绪小人、记忆球和人格岛屿都是什么样子呢……
第二篇
看了《头脑特工队》,
我才知道孩子为什么焦虑和恐惧 作者:塞尔玛·弗雷伯格
正在热映的《头脑特工队》,是皮克斯五年磨一剑的优秀动画片,目前在豆瓣的评分高达8.9分。在片中,具象、生动又非常科学的描述了关于儿童情绪、记忆、性格、潜意识、幻想、抽象思维、梦境等概念。而动画片的主角,则为五个鲜明的情绪小人。
↑ 乐乐 (joy)
↑ 忧忧 (sadness)
↑ 怒怒 (anger)
↑ 怕怕 (fear) & 厌厌 (disgust)
不同人的大脑中,都会有某一个情绪作为主导者,但每种情绪都扮演着自己重要的作用,不同情绪的共同作用,组成一个完整的人格。正如影片中的厌厌对怕怕所说:“情感是不会辞职的。”这样一部影片尤其适合父母们观看。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作为父母,总是希望孩子避免出现消极的情绪。但即便是最理想的养育方式,也难以消除孩子内心的焦虑,更无法扫除孩子的世界里和自身发展过程中无所不在的风险。
人
类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会面临各式各样的伤害和危险。更进一步来说,我们会发现,对孩子生活环境中的妖怪、食人魔和死鹦鹉的过度警觉,并非总是有益于他们心理健康的。许多类似的恐惧都无法避免,而且,也无须避免。当然,谁也不会故意把孩子置身于恐怖之中,也不会让自己的行为举止像个妖怪,从而让孩子对妖怪的想象变得真实。不过,当妖怪、食人魔和死鹦鹉出现时,最好用一种开放的态度对待这一切,并帮助孩子以同样的方式来面对它们。
儿童未来的心理健康,并不取决于他的幻想世界中有没有食人魔,或者食人魔吃什么东西,甚至与食人魔出现的次数和频率也无关。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只取决于他如何解决与食人魔相关的一系列问题。
正是儿童处理自己非理性恐惧的方式决定了这些恐惧对孩子人格发展的影响。如果对妖怪、小偷和野兽的恐惧妨碍了孩子的生活;如果孩子在面对自己想象中的危险时感到无依无靠和毫无防备,并因此形成对生活畏惧和屈服的态度,那么,不难预料,这将对孩子未来的心理健康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如果一个孩子的行为看起来好像受到来自于各种真实或想象的危险的威胁,并且他认为必须加以提防和准备反击,那么,他可能会表现出过强的攻击性和反叛。而且,大人肯定也会觉得他处理恐惧的这种方法很糟糕。
但是,孩子通常都能克服自己的非理性恐惧。而这正是最有趣的问题:孩子是怎么做到的?这是因为,孩子天生就有克服自身恐惧的办法。甚至早在两岁时,他就已经拥有了一套复杂精妙的心理系统,这套系统为他提供预感、评估、防范抵御和克服危险的诸多方法。当然,孩子能否凭借天生的能力成功地克服自己的恐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教他如何运用这种能力的父母。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了解正在成长的孩子的天性,以及他的人格中存在着用于解决问题并有助于促进心理健康的因素,必然能帮助他培养出应对恐惧的内在能力。
在
人类的正常发展中,无论是真实的危险还是想象的危险,都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如果自我未能找到处理危险的办法,就会陷入长期的无助和恐慌之中。对危险的本能反应便是焦虑。在生命之初,婴儿的行为就好像任何意外对他们而言都是一种危险。比如,突如其来的巨响或者被突然暴露于强光之下,都可能让他“吓呆了”。之后,随着婴儿对母亲依恋程度的加深,他会对母亲从自己的视线里消失而感到焦虑,这仍然是一种类似于震惊的反应。大量类似的情形会引发婴儿的焦虑,如果婴儿对所有这一类事情的反应始终都是惊恐和无助的,那么他几乎难以在这个世界生存下来。
但是,很快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危险”的数量减少了。一再重复的经验能帮助婴儿克服危险感,而且“吓呆了”的反应会弱化成类似于轻微的惊奇或惊讶。与此同时,婴儿也开始发展出应对“危险”(这些危险对婴儿而言是危险,对我们成年人而言却不是)的另一种能力。他学会了预期“危险”的到来,并为之做好准备。而且,他正是用焦虑为危险做准备的!
在他睡觉时,母亲离开了。在婴儿发展的早期阶段,婴儿对母亲的离开会表现出某种焦虑,这是因为母亲从自己的视线中消失而引起的吃惊或震惊。在婴儿发展的后期阶段,一旦他靠近自己的床,甚至只要是走进自己的房间,他就会产生某种焦虑,继而哭闹和抗议。他已经预见到母亲会离开这件可怕的事情,并通过在事情发生前产生焦虑让自己做好准备。这种由预期而产生的焦虑能帮助他应对与母亲分离的痛苦。我们有理由相信,与早期每次把与母亲的分离都当作一件让他感到吃惊和震惊的事情相比,以这种方式预期分离能减少它给婴儿带来的痛苦。
由此,我们应该认识到,焦虑本身并不是一种病态,而是个体在应对危险时,采取的一种必要而正常的生理和心理准备。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缺乏预期焦虑反而可能引发神经症!那些被战争的惨烈吓跑的人,正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没有发展出必要的预期焦虑,让他对危险做好准备,从而无法避免创伤性神经症。在某些情况下,焦虑对于人的生存是必不可少的。对危险缺乏理解,不能为危险做好准备,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后果。而且,我们发现焦虑有助于人们实现其最高目标。事实上,表演艺术家在登台前的焦虑可能会促使他们在表演时发挥出最高水平。
焦虑有益于孩子的社会性发展,它是孩子获得良知的动机之一。正是因为害怕被所爱之人批评以及对被爱的渴望,让孩子形成了良知;正是由于害怕良心的谴责,才促使人们做出符合道德标准的行为。最初,正是出于对种族灭绝的焦虑,人类的不同群体为了彼此的安全而紧密生活在一起。我们可以用一长串人类发明和人类机构的清单,继续证明危险以及对抵御危险的必要,以及它们如何提供了人类追求最高层次文明的动力。当然,我们知道,焦虑并不总是有益于个人或社会。无法应对的危险会让人感到无助和失去信心,导致逃避或者反社会行为。只有在这些情况下,我们才可以把焦虑视为病态。不过,更为准确的说法是,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者试图用这种办法解决问题的行为是病态的。
所以,让我们回到促进孩子心理健康的目标上来,理解出现在童年早期的恐惧的本质,并且仔细观察孩子们用来应付危险的办法,这些危险出现在孩子发展的各个阶段,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想象的。
第三篇《头脑特工队》背后的儿童心理学
原刊于:纽约时报刚刚上映的《头脑特工队》,是今年最适合父母们去看的电影,这部pixar的新作目前在imdb目前的评分高达8.5,而且是近年来pixar少见的精品作品。
不过更重要的是,这部动画片对儿童心理学的描画,顶的上读好几本学术专著的收获。在动画片中,具象、可爱又相当科学的描述了关于儿童性格、情绪、行为、记忆、潜意识、梦境、幻想、抽象思维等等概念。而动画片的主角,则是五个鲜明的情绪小人:喜悦joy、悲伤sadness、愤怒anger、恐惧fear和厌恶disgust。
不同人的大脑中,都会有某一个情绪作为主导者,但每种情绪都有自己重要的作用,不同情绪的共同作用,组合成一个完整的人格。这部电影的科学性基础,是来自两位著名心理科学家:著名的微表情专家,美剧《别对我撒谎(lie to me)》的主人公原型paul ekma,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大学的心理学教授dacher keltner。今天我们听听他们如何讲解《头脑特工队》中的心理学概念。(原文发表于纽约时报,标题:头脑特工队的科学,the science of ‘inside out’。)
五年前,pixar的编剧和导演皮特·多克特联系到我们,介绍了一个他们的影片构思:用动画描绘一个人的情绪是如何在头脑中工作,并是如何同时表现在一个人的外在社交生活中的。
他设想的主人公,是一个正在经历生活中艰难阶段的11岁女孩。作为研究了情绪几十年的科学家,我们很高兴他找到我们。而我们作为顾问的这部作品已经完成并最近上映,就是《头脑特工队》。我们与多克特先生和他的团队的沟通主要是关于影片核心的科学问题的:情绪如何管理意识流?情绪如何给我们过去的记忆上色?11岁的小女的情感世界是怎么样的?(科学研究发现,从这个年龄开始,积极情绪的强度和频率开始急剧下降)《头脑特工队》是关于5种拟人化的情绪——愤怒,厌恶,恐惧,悲伤和喜悦——是如何解决一个刚从明尼苏达搬到旧金山的11岁女孩“莱利”的心理动荡期。 (我们曾经建议影片包括现在科学研究的所有情绪,但被多克特先生拒绝了,理由很简单:这个故事只能处理5-6个角色)。
本片的两大主角:joy和sadnes莱利的性格是由喜悦joy来主要决定,这是与我们所知道的科学相符。
研究发现,我们的个性是由特定的情绪所定义的,这形成了我们感知世界的方法,我们表达自己的方法,以及我们回应他人的方法。
但影片的真正明星是sadness 悲伤。《头脑特工队》是一部关于失去,关于伤感会让人获得什么的电影。莱利离开了在明尼苏达的朋友和她的家。
更尖锐的是,她已经进入了青春期前的阶段,这让她开始告别童年。我们对sadness的描写确实有一些冲突性,她被看作是一个拖累,一个喜悦joy一直试图从莱利的意识中拖走的角色。事实上,研究发现,悲伤和重要的生理觉醒有关,激活机体对失去的反馈。在影片中,sadness看上去很土和让人倒胃口。但现实生活中,更多时候一个人的悲伤会让她获得其他人的安慰和帮助。放开这些不提,电影中对悲伤描写,成功地将情绪心理学中两个核心观点用戏剧手法表述出来。
妈妈心中,是由悲伤sadnes主导的
首先,情绪会组织而不是破坏理性的思考。西方传统思想史上,普遍的观点认为情感是理性的敌人,破坏社会的合作关系。
但事实是,情绪指导我们认识世界,指导我们对过去的记忆,甚至指导我们用道德判定对错,最典型的方式,并且让我们可以对当前形势做出快速有效的判断。
例如研究发现,我们愤怒的时候,可以更敏锐注意到不公平的事情,这有助于我们纠正不公正的行为。在《头脑特工队》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sadness悲伤逐渐掌控了莱利的对于目前生活变化的思维处理。最明显的是当sadness往莱利在明尼苏达州的回忆中增加了蓝色。科学研究发现我们现在的感情塑造了我们对过去的记忆。这是电影中sadness的一个重要功能:她引导莱利了解她正在经历什么变化,她失去了什么,这为莱利创造了搭建新自我人格的舞台。
爸爸心中,是由anger愤怒主导的其次,情绪会组织而不是破坏我们的社交生活。
例如有研究发现,情绪搭建出(不只是上色哦)各种社会关系间截然不同的互动:父母亲子关系,兄弟姐妹冲突,年轻人间的调情,以及对手之间的谈判等等。
也有研究发现,在社会集体抗议不公、捍卫权利的过程中,愤怒是一种远比政治认同感更有效的推动力。而我俩中一人的研究发现,当我们不小心违反社会规范时候,表现出尴尬的情绪,会更容易得到别人的原谅。
这些概念也在电影中戏剧化地表现出来。你可能倾向于认为悲伤是一种被动、不作为的状态,是一种没有任何目的的行为。但在《头脑特工队》和现实生活中,悲伤提示人们团结在一起面对失去。
影片前面的餐桌场景中,愤怒的争吵导致莱利离开不知所措的爸爸,冲进楼上独自躺在黑暗的房间里。而在影片的结尾,是悲伤让莱利和父母团聚,用拥抱触摸的形式和包含情感的声音,传达出团圆的喜悦。
《头脑特工队》提供了一个新的处理悲伤的方法,核心就是:拥抱悲伤,让它展露出来,耐心的处理青春期前儿童的情感斗争。悲伤会让我们认清那些已经丢失的事物(比如童年),让包括孩子和父母的全家人去收获他们所得到的:未来新自我的舞台基石。
关注“兰舟育儿的那些事”,微信号:yymm-lzye 为您分享专业的育儿知识,儿童心理,亲子生活,人文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