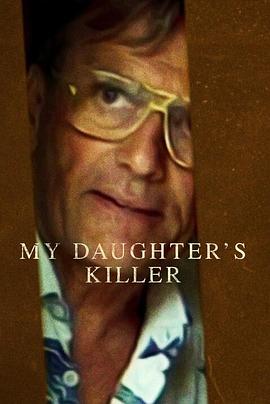剧情介绍
三角恋听多了,三个人还能都登报声明互相祝福、转身交朋友,这操作你见过没?偏偏是在1920年代的上海摊头,还弄出一长串“启事”来,闹得人家报纸编辑都得反复揉眼睛。说老实话,这一出连咱们如今追的青春偶像剧都得甘拜下风——你看完,很可能和我一样,脑袋嗡嗡直响:先别动,我还没想明白。
 "
" 那年头,上海的冬天还留着点江南湿冷的韵味。1924年11月末,三天之内,《民国日报》上硬生生地蹦出三则互相关联又莫名其妙的“告示”,热闹得让隔壁邻居老太都得搬个小凳儿来研究。第一天,说是杨之华和沈剑龙“各奔前程”,把娃娃亲给拆了。第二天,杨之华和瞿秋白这俩人堂而皇之地宣布恋爱。第三天,沈剑龙和瞿秋白来了场“世纪大和解”,从“情敌”直接变成了哥们。
这三个人,原本想来也就是同一座城里的陌生人。只是谁能想到,戏剧就开在了杨之华人生的第一幕。
杨之华的起点,是典型的旧式大家闺秀。爹娘给安排妥当,下一本“沈氏”的户口本,算是小时候打断的娃娃亲上线了——纸婚,早得出奇。沈剑龙,长得俊俏,念书也有几分姿色。但归根结底,他的底子里搁的还是沈家的“父凭子贵”和男人的撒野。从一开始,杨之华就觉得这家门不太像自己能靠岸的港湾。
沈剑龙呢,十来岁读书时山水有灵气,诗书气自华,兴许偶尔还能作首清词小令。可惜这点文气在后头成了“锦上添花”——家底厚,父亲沈定一是有名的风流人物,一屋子妻妾成群,儿子长大后“脚步跟着心走”,不把规矩放在眼里。杨之华进了上海大学,整个人像鸟一样终于有了天。反倒沈剑龙,空了屋子更没个拘管,在家乡折腾出不少花边新闻。传话到上海,杨之华摞下一沓摞一沓信,苦口婆心,没来得及落地,转头就被沈定一干脆退回。
我有时候会想,杨之华那时心里是不是已经认命?夫妻表面风平浪静,其实两人隔着一条浑浊的河,横看纵看都是平行线。所有的“努力”,最后都成了自己和自己较劲。
沈家外人看着“绅士风度”,无人诉说杨家姑娘心里的委屈。杨之华的妹妹怜她,常和娘家人讲:“这些年姐姐只剩挣扎,哪谈得上爱。”沈剑龙对感情不再负责,杨之华把头埋进书里,越学越清醒——心跳的节奏变了,做梦都不愿回沈家大宅。
1921年,有了独伊。杨之华给她取这样的名字,大概是早已经决定了,“独”为独立,“伊”为自己此生唯一的骄傲。沈剑龙的世界温柔不了她,她开始悄悄合上过往,把未来攥在自己手里。
这段时间,瞿秋白的生活也翻江倒海。他的第一任妻子王剑虹,那是青年革命者圈子的明星人物,俩人一拍即合,短暂而火热——理想、爱情、诗意都不缺。可惜天意弄人,王剑虹患上肺病,仅仅过了七个月,就带着所有的柔情走了。瞿秋白写信给丁玲,说自己的心也随她而去。那一刻,钢铁意志的大革命者,不过是个哀伤的年轻人。
说来缘分,王剑虹与杨之华也不是路人。1922年,杨之华鼓足勇气独自赴沪,投入女权运动,热心四溢地结识了向警予、王剑虹、还有丁玲。那个年代有点意思,女孩子自带铜墙铁壁,男同志温文尔雅。很快,杨之华考进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偏偏瞿秋白就是她的系主任。
杨之华求知若渴,课堂上盯着讲台上的瞿老师,心里多少也泛波澜。两人下课后交流,渐渐熟了。瞿秋白为人温和,没什么架子,哪怕是在社会风气还守旧的年代,也乐于帮她引路入党。
越了解,就越发现彼此像“同道中人”。可也就是因为这份情愫,杨之华内心拉扯到了极致。她明知道自己已经是人妻,为了不让关系闹大,干脆悄悄回了老家,透一口气。你以为瞿秋白会就此冷静下来?偏不。他铆足了劲挑明了道理——沈剑龙的事情是他自己作出来的,杨之华如果想幸福,干吗非得顾忌那些死规矩?
于是人家瞿秋白也来了个“放手一搏”,背着行李干脆直奔杨家老宅,非要挑个明明白白的说法。巧就巧在,这天沈剑龙也在。外人以为俩男的会一言不合,拳脚相加,其实最多是喝口茶,你一言我一语,世界突然平静下来。最后,三人坐下来,协议签好,报纸一登,各安天命。
1924年秋末,杨之华和瞿秋白在上海简单又庄严地办了婚礼。沈剑龙竟大大方方来祝福,还真成了朋友。沈剑龙后来送瞿秋白一张照片:剃了光头,袈裟一披,手里献花,背后留言“鲜花献佛”——你说俗不俗,倒也算难得的体面。
可高兴归高兴,杨之华的父母却气得铁青脸,觉得有伤风化,直接拉黑了亲闺女一回。沈家更不服,老爷子沈定一那点男权思想拧在心里,儿子胡来无所谓,儿媳妇再找幸福却无论如何不允。孙女独伊?不能说带走就带走——杨之华,离婚归你,孩子归我。这老一套的家乡逻辑,偏偏打到了女人命门。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杨之华看女儿只能偷偷摸摸,婆婆还算好心,带她见了几面。可小姑娘抬头一句:“妈妈,我的妈妈已经死了。”那一瞬,杨之华眼泪像断线的珍珠。母女隔着规矩和时代,谁都无力。
好在世事留有转机。不久后,独伊终于被接上海,跟着妈妈和继父瞿秋白生活。你可以说她命不好,也得说她碰上了一个好“爸爸”。瞿秋白不是她亲生父亲,可却从没拿她当外人,教她认字、画画,经常亲自接送幼儿园。那时小姑娘天天和茅盾家的沈霞作伴,一个文学圈的小团体,气氛说不出的好。
倒是时代不肯给小家庭太多温情。两个大人每天都投身工运、革命事务,独伊渐渐习惯了一个人在国际儿童院生活。母女通信,瞿秋白偶尔寄来明信片,留言总带着革命理想味儿:“你将来也要为新中国造飞艇。”日子并不总顺。但幸好记忆中还有一些温存。
后来风浪大作。1934年,长征拉开大幕,瞿秋白本想跟着中央红军同行,却没获批准。局势险恶中他辗转离开瑞金,结果路上被人出卖,最后落入国民党和地方势力之手。
酷刑、威胁全都用上了,说白了就是要破防他的意志。可瞿秋白始终咬死了最后的底线——生死置之度外,党的一丝秘密也不肯吐露。到1935年6月,凶令下,瞿秋白赴死前,毫无屈服。那个《多余的话》写尽无奈,更多是这一代人的孤勇。
独伊后来在报纸上看到父亲殉难的讣告,眼前一黑,整个人摔倒在地。她没能见到继父的最后一面,但这份父爱却成了她此生的老本。
生活推着母女往前赶路。1941年,她们跟母亲转战大西北,却又在新疆被盛世才下狱。这一关就是好多年,甚至要等到抗战胜利后才终于放人。
奇怪的是,命运有时爱开玩笑。独伊在牢里遇见了同是政治犯的李何,演了一出狱中情缘。两人一出狱,便一道加入了共产党,继续各自的信仰生活。瞿独伊成了新华社的战士,挺得住风风雨雨,却总逃不过情感和命运的跌宕——丈夫去世,儿子又骤然病逝,一年之内两大噩耗,谁都得熬一熬。
历史没有完全放过她。“文革”之后,她见到宋希濂——就是那个执行枪决令的将军。宋希濂竟然低头不语,只余尴尬一脸。而也是那时,瞿独伊才完整拼凑出父亲瞿秋白最后的故事。
杨之华,一生的命都写在了丈夫墓碑上。久别重逢,1955年她终于找回瞿秋白的遗骨,亲自送到八宝山。后来有人问她,为什么再没结婚。她只是淡淡一句:“世上,再无秋白这样的人了。”
我常常想,独伊和她母亲,失去的东西太多,得到了却也算几份温柔。命运谁能算得明白?也许那些错综复杂的“启事”,早在多年后化作纸烟,天光里只有女儿依旧在想念父亲,母亲守着一生的承诺。
或许,我们都想错了。真正留存下来的,恰恰是那些人与人之间不肯轻易松手的爱与倔强。
你再想想,如果来回穿梭于这些年来的江湖,那些交错的善意和别离,你我或许都说不明白。只剩下心里那句,“别急,我还在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