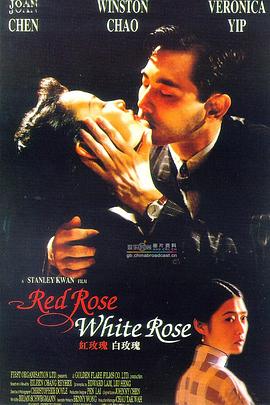剧情介绍
事实上,在被大众传媒及其受众以堪称狂热的盎然兴致命名为“世界末日”的时刻(2012年冬至日)降临前后,除了拉娜?沃卓斯基、安迪?沃卓斯基、汤姆?提克威联合导演的《云图》,还有两部引人瞩目的欧美大制作电影也在全球各大院线的银幕上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呈现了名曰“革命”的景观、讲述了关于革命(及其失败)的故事,它们是“好莱坞最后的电影作者”(斯皮尔伯格语)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的《黑暗骑士崛起》,凭《国王的演讲》赢得2011年奥斯卡小金人的汤姆?霍伯导演的《悲惨世界》。[6]当然,这三部电影的革命叙事有着诸多不同,限于文章篇幅,在此难以尽述。仅就主要革命者形象而言,《黑暗骑士崛起》中的革命/叛乱军领袖贝恩,在文本的动素模型中明显处于(主体/英雄之)“敌手”的位置;而《悲惨世界》中唯一幸存的起义者马吕斯,在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下也只不过是一个虽一时离轨但最终扬弃了革命、回归了家族的特权者;与上述二者不同,正如前文所论述的,《云图》中的星美-451是一个处于阶级/性别/种族三重受压迫状态、经历文化启蒙并最终彻底觉醒的革命主体。
而与大卫?米切尔的原著相比,沃卓斯基姐弟和汤姆?提克威编导的电影文本固然保留了星美-451作为革命主体的主要特征,但与此同时,他/她们对《星美-451的记录仪》这部分还做出了十分重大的改动,其中最为显著的改动就是张海柱这个角色:他集原著中的司机张先生、梅菲教授和任海柱中校的行动范畴于一身,以“张海柱上校、联盟会首席科学官”的身份充当了星美-451的施惠者和帮手;最关键的是,他不再是奥勃良(《一九八四》)式的“演员”/特工,而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他在理想的感召下竭尽所能地以卓越的学识去对决庞大的权力机器,把自己的满腹经纶、满腔热血全都献给了为克隆人乃至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的壮丽事业。张海柱投身其间的联盟会也不再是“兄弟会”式的阴谋伪装,而确确实实是一支致力于解放事业的革命力量。
但相较于国家机器,这股力量是何其微弱;面对公司国的猛烈炮火,联盟会的掩体就像《悲惨世界》中的巴黎街垒一样难堪一击。或许是沃卓斯基姐弟的审美偏好与文化政治取向所致,联盟会的领袖安高?阿比斯与沃卓斯基兄弟[7]的另一部反乌托邦大作《黑客帝国》(1999/2003)中人类反抗军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墨菲斯同为黑人、外形相近;而张海柱的扮演者——英国演员吉姆?斯特吉斯化妆为东方人之后,其相貌酷似《黑客帝国》的主角尼奥(或需赘言的是,尼奥/the one的扮演者基努?里维斯并非所谓“西方白种人”,而是融合了英国、爱尔兰、中国,夏威夷土著、葡萄牙多种血统的混血儿)。但《星美-451的记录仪》[8]与《黑客帝国》尤其是其第三部《矩阵革命》之间更重要的互文关联在于:二者所想象的未来革命皆以失败告终。诚然,“人们战斗,然后失败。尽管失败了,但他们为之一战的事情出现了。”(威廉?莫里斯语)但是否一如《黑客帝国》三部曲所喻示的,反抗奴役的斗争终究只是统治机器更新换代、系统升级的一个必要程序?是否一如雅克?拉康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的,反叛资本主义体制的左翼抗争终究难以逃脱“对注定要失败的事业的自恋”?《云图》里不同时空交叠演绎的压迫/反抗六重奏,是否只能引申出一幅“永劫轮回”的人类命运图式?
超逸轮回的端倪或许正在于电影版《云图》对《星美-451的记录仪》的另一处重要改编:星美-451与张海柱的超越生死之爱。旧有的人类文明湮灭之后,星美化作手擎火炬的自由女神云石塑像,以她的“启示”指引着幸存者探求新生;在这个意义上,雨果颂扬安灼拉的赞词——“自由女神云石塑像的情人”,对于张海柱而言就不只是一个隐喻性的修辞,而的的确确名副其实。如果说,“爱情”一方面犹如一叶亮丽的“金色方舟”,将现代文化涉渡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与个人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一方面也作为抵抗启蒙现代性、工业文明功利主义的审美现代性、浪漫主义文化的母题之一,始终承载着非/反(工具)理性的意蕴,携带着某种颠覆性的质素,因而成为文化霸权时常倚重却间或难以挥洒自如的双刃之剑;那么,迥异于《悲惨世界》中(珂赛特与马吕斯的)爱情神话发挥着瓦解革命意志的离心力,并最终以异性恋婚姻的美满和父权制家庭的团圆成为革命青年/离轨者回归秩序的归宿,相似而又不同于《黑暗骑士崛起》里(贝恩与米兰达/塔利亚的)爱情作为一种绝对的驱力构成威胁既存秩序的疯狂之源,成为捍卫主流社会核心价值的超级英雄必须清除的可怖魔障,《云图》所歌颂的大爱正是一种超越阶级(律师与奴隶、科学官与服务生)/种族(白人与黑人、“纯种人”与克隆人、高科技文明的黑人“先知”与低科技文明的白人土著)/性别(同性恋)[9]之“界限”、破除社会达尔文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异性恋中心主义之“常规”的解放性力量。在这里,沃卓斯基姐弟不再像10年前编导《黑客帝国》系列的沃卓斯基兄弟那样,使用深情呼唤“我爱你”就能令人死而复生的俗套来实现意料之中的戏剧性逆转;她/他们和汤姆?提克威联合编导的《云图》中的“爱”,并不具有起死回生的魔力,但它作为一种不朽的信念却是连死神也绝不可能抹杀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爱比死亡更长久”(love could outlive death)。
也正是在永垂不朽的意义上,《云图》中由那六枚流星胎记串联起的,绝非宗教意义上的投胎转世,而是经由文化文本——亚当?尤因的日记、罗伯特?弗罗比舍的书信、路易莎?雷的传记、由蒂莫西?卡文迪什的自传改编的电影、星美-451的记录仪、扎克里的口述史——传承的、生生不息的人文精神:那是以死继之的抗争意志,那是对于自由和平等的永恒追求!由《云图六重奏》(cloud atlas sextet)而《云图进行曲》(the atlas march)进而《云图终曲》(cloud atlas finale),在《云图》这部复调电影的终曲处,伴随着主题的密接和应,六重命运在快速剪辑中并置叠加;曲终时刻,非线性的叙事最终回到了(线性)时间轴上的起始事件,《云图》情节线索中第一位“自我解放的奴隶”奥拓华的挚交好友、决心投身于废奴事业的亚当?尤因,面对代表着强权秩序的岳父的淫威逼问,不卑不亢地答道:
汪洋何来,若无诸众的水滴?(what is an ocean but a multitude of drops?)
这是以“1-2-3-4-5-6-5-4-3-2-1”的“山峰式叙事”结构全篇的小说《云图》的画龙点睛,这是采取交叉剪辑的方式、以音乐的韵律感引领叙事节奏的电影《云图》的曲终奏雅。
在这里,笔者将multitude译为“诸众”,参照的是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在《帝国》(2000)和《诸众》(2004)中提出的概念。不同于在世俗实践中始终被现代国家政治规则牵引着的“人民”概念,“诸众”虽然也是关于“多数人”的建构,但其众多性并不仰赖于任何的普遍性和同一性,而是生成于德勒兹意义上的特异性和多样性;它是由特异而多样的个体有机聚合成的多数人,抵抗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新帝国金字塔。不同于具有经济决定论倾向和排他性的“工人阶级”概念,“诸众”试图在全球性的资本、劳工流动消解(经典政治经济学中)形成阶级之基础的历史语境下,指认政治主体的多样可能性;在“诸众”的政治视野中,无论是产业工人,还是从事其他劳动形式的各种生产者,无论是阶级层面的受剥削者,还是种族层面的受奴役者、性别层面的被压迫者、年龄层面的遭放逐者,都有可能自我塑造、自我实现为历史的主体,都有可能参与到改造世界、创构未来的政治实践中。
在这个意义上,“诸众的水滴”是对于“解放主体”(emancipatory subject)的召唤。如果说,大众传媒炒作的“2012天灾”并没有降临,但早在2012年(《蒂莫西?卡文迪什的苦难经历》的时间节点)之前就持续推进着的累累人祸却将导致人类文明的“陷落”;那么,避免“末日”的可能途径就在于,从过去到将来诸众抗争的积流成海涤荡邪恶势力的污泥浊秽,因为,正如星美-451所启示的:“我们的生命不只属于自己,从子宫到坟墓,我们都与他者相连,无论过往还是此时,每一桩罪行、每一项善举,都重生着我们的未来。”——沃卓斯基姐弟与汤姆?提克威在改编文本时新增的这番哲思,令《云图》比起沃卓斯基姐弟编剧的那部优雅而孤绝的反乌托邦电影《v字仇杀队》(2005)[10]要更上一层楼,并且在反乌托邦那取代了天空也遮蔽了未来视野的人造穹顶上打开了一处豁口,敞向一个充满变数的开放性的未来……
诚然,《云图》抒发的“只是”一种信念,但请不要忘却维克多?雨果为我们留下的箴言:“没有什么比信念更能产生梦想,也没有什么比梦想更能孕育未来”。如若要为这一信念添上现实的参照,请透过文化镜城上那些难以弥合的裂隙放眼望去:在所谓“历史终结”的今时今日,诸众的抵抗并未失陷于永远封闭的现在时迷宫之中,在自由广场,在解放广场……新的历史篇章正在开启,或者说,必须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