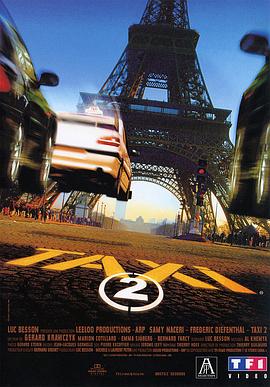剧情介绍
巴黎可能是一个危险的旅游地。据说日本人特别容易罹患医学上所谓的“巴黎综合症”,这种疾病会使那些期望值过高的人感到人格分裂、焦虑和晕眩。苏联人虽然不像日本人那么容易崩溃,但他们将巴黎视作文明、文化的朝圣地,在巴黎投资甚巨。尽管苏联对资本主义不屑一顾,但对西方文化遗产的深深尊重已融入了苏联体系。唯一的问题在于,苏联的边界是封闭的,斯大林对西方文化的高度欣赏只能等同于对退化的艺术“形式主义” ——也就是现代主义——的排外式恐惧。但在后斯大林时期,在赫鲁晓夫的解冻时期,“与西方和平共处”——正如埃利奥诺里·吉尔伯德所说——与人类文化的“普遍性”和“世界文明”的价值一同成为了新的正统观念。
《有生之年看巴黎:西方文化影响下的苏联生活》书封,作者:埃利奥诺里·吉尔伯德
由英国文化委员会管理的文化交流活动是通过1959年的一项苏英协议建立的——1966年还是一名研究生的我是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受益者。这项文化交流活动补充了此前在全国学生联合会主持下组织的小规模访学,同时一项新的、谨慎的、鼓励性的国际旅游政策将外国人带到了苏联,也将有限的苏联游客在严密控制下带到了西方。
《外国文学》杂志向苏联读者介绍了欧洲和美国作家的翻译作品,广受欢迎(人们真正想读的杂志是一种稀缺商品)。在书中,苏联读者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斯科特、雨果、狄更斯、大仲马、巴尔扎克、吐温和雷马克的作品。在俄罗斯和苏联传统的鼓励下,苏联人按照文学作品来过自己的生活,并以虚构的主人公为榜样,他们满怀热情地进入了这些文学世界,发现了海明威笔下主人公模糊的情感困境,就像他们与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作品中“积极的英雄”宣扬的直接斗争一样。当海明威在1961年夏天去世时,苏联媒体“哀悼一位民族英雄的去世,这是海明威在美国和古巴之外都没有得到的待遇”。《麦田里的守望者》发行了几个版本,发行量很大,但像往常一样,需求远远超过了供给,这本书的黑市价格几乎是官方价格的30倍。雷马克的《三个同志》于1958年以俄语出版,正如一位苏联当代人所说,成为“一代人的小说”。它对男性友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退役士兵之间的友谊)和命中注定的爱情的描述被“视为一种启示……‘我们在雷马克中读到了我们自己,这部小说是关于我们的。'”
1957年8月的“莫斯科青年节”吸引了34000名外国人到莫斯科停留了两周,对西方的向往终于转化成了与西方人接触的狂喜时刻,这是一代人生活的分水岭。在此期间,对外国人的严格控制在很大程度上被取消了:边境无需行李检查,无需填写货币申报单,甚至不需要正常的签证,任何被国际青年运动相关委员会选为代表的人只需从他们当地的苏联领事馆领取一张保证入境的卡。苏联无权否决由国家委员会选出的代表,即使他们被告知“可疑人物”正在路上——包括“来自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和来自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党人、来自西班牙的长枪党党员和来自英国的帝国忠诚者,以及来自世界各地虔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们可以自由漫步到莫斯科郊外的节日场所(比如莫斯科北郊的khimki,1957年前禁止外国人进入,之后几十年也禁止外国人进入)。艺术节的艺术策划者们复兴了自20世纪20年代辉煌时期以来的前卫冒险精神,他们灵感迸发,将卡车和公共汽车画成了“橙色、蓝色、黄色、淡紫色”,并添加了“带有蓝色波浪条纹的异国花卉、鸟类和蝴蝶”。对习惯了单调和灰暗颜色的人来说,这是彻底的文化冲击。一名莫斯科人回忆道:“以前,我们在莫斯科只知道伪装过的卡车,好像它们都做好了接受紧急动员、开到军队里去的准备。”
尽管有三万名共青团员在街上排队维持秩序,莫斯科人和西方人之间的第一次相遇依旧是狂热的。当涂上“不可思议颜色”的卡车把代表们从城市北部的酒店带到南部新建的卢日尼基体育场参加开幕式时,人们——甚至共青团员——爬上卡车,把花束推到公共汽车的窗户上,把西方人拉出来拥抱,并被拉进即兴的舞蹈和歌唱中。莫斯科街上的一幅标志性图像显示,两个美国女孩手牵手跳舞,其中一个赤脚,而一个美国男孩在班卓琴上演奏着俄罗斯民歌“喀秋莎”。
后续影响是,为了弥补节日期间被冷落的窘境,克格勃加强了对当地人的监视,怀疑当地人与外国人建立的可疑的密切关系。1967年,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那时紫色的卡车早已从街上消失,这个节日也只是一个梦幻般的记忆,但是与西方文化联系并成为世界文明一部分的冲动仍然存在——有时受到政府限制,但经常是受到鼓励的。意大利和法国电影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苏联上映,使热拉尔·菲利普、伊夫·蒙当和西蒙·西涅莱成为被崇拜的英雄。费里尼的《八部半》赢得了1963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的大奖,尽管有些人对这一选择感到愤怒。据报道,赫鲁晓夫在这部电影放映期间睡着了。
伊夫·蒙当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举办了非常成功的音乐会。他的歌曲“c'est si bon”和“les grands boulevards”反复在电台播出,是苏联版本的巴黎神话的核心。同样有影响力的是亲法派作家伊利亚·爱伦堡的回忆录,该书于20世纪60年代在《新世界》连载,书中他深情地回忆了世纪之交在蒙帕纳斯的日子:“爱伦堡的巴黎在12月有灰色的建筑和绿色的草地。这里住着街头歌手、接吻的夫妇、在咖啡馆消磨时光的可敬老人、戴着巨大羽毛装饰帽子的女人、淘气的学生和贫穷的艺术家。”爱伦堡是法国印象派的热情倡导者,在斯大林晚期被认为不够现实,但被他描绘成真实和真诚的(都是“解冻时期”的核心价值观),“渴望看到新的自然,以不同的方式描绘它”。普希金博物馆开始从仓库中取出印象派绘画,随后苏联和法国的大型展览接踵而至。印象派的巴黎、爱伦堡和伊夫·蒙当都融合在浪漫的苏联城市神话中。
20世纪50年代中期也带来了比印象派更难理解的东西:毕加索,他的作品(他自己选择的)于1956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展出,并引发了激烈的争议。用苏联的话说,毕加索很复杂,因为他既是共产主义者——著名和平鸽的制造者——又是“现代主义者”,其艺术风格对苏联画廊的观众来说是陌生的。一些人认为他的作品代表了与斯大林主义历史的典型决裂;其他人认为它丑陋而反常。这是一个有趣的论点,因为这一次争论不再由国家主导,激烈的辩论发生在学生宿舍、编辑部,甚至城市广场,观看展览的队伍非常庞大。“喧哗与骚动”的氛围在当时的报道中很突出,因为人们聚集在博物馆周围,听“古怪的年轻人热情地捍卫现代主义,而同样认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卫士试图贬低他们”。
吉尔伯德的散文最生动、最能唤起人们对喧哗与骚动的描述,比如莫斯科青年节和毕加索展览,而她关于文化接触机制的章节则是“力量之旅”。以翻译为例:苏联有自己的方法,将翻译的功能转换为“再生化身”(perevoploshchenie)的概念,有点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著名的表演理论。原则是“外国作品的每一次翻译都必须成为俄罗斯文学的一种现象”,不仅仅是对文本的再现,“更重要的是对原作的体验”。这是一种富有想象力的再创造行为,涉及译者的主观输入。编辑亚历山大·塔多夫斯基在谈到诗人萨缪尔·马尔沙克对伯恩斯的翻译时说,尽管保留了伯恩斯作为苏格兰人的声音,马尔沙克仍然“使他(伯恩斯)成为了俄罗斯人”。如果我在20世纪60年代没有听到苏联吟游诗人尤里·金演唱马尔沙克版的a·米尔恩的克里斯托弗·罗宾的诗歌,我可能会认为那仅仅是一种华丽的辞藻,对我和莫斯科观众来说,这种诗歌竟然奇迹般地转变成了一种明显的俄罗斯风格。马尔沙克的版本去除了原作的矫情,充满了情感的深度,比米尔恩的要好,这也是苏联翻译家的目标。丽塔·莱特-科瓦列娃翻译《麦田里的守望者》时从未出过国,但她认为霍尔顿·考菲尔德是“一个激动、温柔和纯洁的灵魂”,将他翻译成俄语以独特地表达他“可爱、纯洁的声音”。吉尔伯德通常对自己的个人偏好保持沉默,但听起来她似乎更喜欢俄罗斯版的童年,而不是原版的:她写道,莱特·科瓦列娃的译本“更丰富、更富表现力、更富感情色彩”,而俄罗斯霍尔顿·考尔菲德“比他的美国原型有更广阔、更精确、更令人惊讶的词汇:他也更敏感、更深情、更脆弱。”
吉尔伯德说,大多数在苏联上映的外国电影都被配音,不是出于审查的原因,而是出于“对形象完整性的美学关注”和从1920年代苏联先锋派继承下来的“框架总体性”。苏联配音演员无法与文学翻译家的很高的文化地位相比,电影媒介本身限制了外国世界被重新想象成俄罗斯(苏联)世界的程度,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尽了最大努力,讨论了“音乐性和节奏词汇”中的配音,并认为他们的工作面临的挑战类似于诗歌翻译的挑战。他们的任务是让苏联观众在情感上和字面上都可以理解这部电影,有时还需要英雄主义的措施。在由杰拉·菲利普和吉娜·劳洛勃丽吉达主演的《郁金香芳芳》的苏联配音版中,配音员吉娜·乔特提供了一个完全脱离原著的画外音叙述者——“一个新角色,一个苏联的发明,被创造出来解释这部电影的表演”——这部苏联版的幽默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配音员。苏联配音导演的目标是让他们的版本比原版更好,要“心理上更深刻,情感上更易共鸣”。
尽管去西方的苏联游客数量相对较少,但也在不断增加,其中包括许多苏联作家。他们通过在文学和绘画中的再现,将欧洲的大城市描述为一见如故却不为人知的。巴黎是苏联人最了解的城市,从左拉的小说和爱伦堡的回忆录到1960年在莫斯科举办的摄影展《活着的巴黎》,都是苏联人了如指掌的文化事件。吉尔伯德写道,对于苏联艺术家、作家和读者来说,巴黎首先是记忆,然后才是体验。事实上,有时真实的经历令人不安(巴黎综合症的阴影!),当这座城市的林荫大道上挤满了美国游客时,巴黎“喧闹、无知、自鸣得意、重商主义”,古老建筑的外墙被“花哨的海报”弄得面目全非。
*
苏联与西方的爱情注定以失望告终。一旦俄罗斯人可以自由旅行甚至移民,如果他们负担得起,还可以永远住在巴黎,逐渐地,巴黎就不再是苏联的文化梦想了。有时候,对于20世纪90年代迷失方向的移民来说,这更像是一场噩梦。新移民把他们喜爱的左拉和巴尔扎克的多卷本译本拖出俄罗斯后,突然发现它们与现实毫无关联,甚至令人尴尬。原来,“他们的”巴黎——他们的普世文化——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苏联对西方的文化想象变成了“与其他苏联劣质事物相似的旧垃圾……人们知道他们的文化偏好已经过时,他们的生活方式依然幼稚……他们一心一意地培养文化资本,但发现自己两手空空。”他们觉得自己是西方文化遗产的“拥有者”,但事实证明,这种拥有只存在于他们的虚幻梦境里。
吉尔伯德认为,“苏联和西方的乌托邦一起解体了”——这是她描述的矛盾情况之一。对西方文化的热爱并不包括对自身主权的否定。相反,热爱西方文化是苏联文化的象征,这是每个受过教育和培养的苏联公民都应该具备的素质。任何被问到沃尔特·司科特或西奥多·德莱塞的小说的来访外国人都会证明,苏联公民通常认为他们比西方本地人更了解西方文化(或至少是典型的苏联版本),并且更喜欢西方文化——他们是对的。此外,他们觉得这种文化欣赏能力本身就是他们国内文化的产物(他们有时会把这种文化称为“苏联文化”,有时称为“俄罗斯文化”),他们也是对的。有些俄罗斯人喜欢资本主义,但吉尔伯德描写的不是受教育的俄罗斯人或苏联知识界,她所描述的“所有权”类型,包括对文化商品的非物质的和共享的集体拥有,看上去是资本主义的;但事实上无疑是“社会主义的”——尽管已故的苏维埃实践者通常倾向于避免使用这个词(因为害怕听起来老套)——它完全符合苏联社会主义传统,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俄罗斯第一任启蒙运动人民委员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
《有生之年看巴黎》是一部高度个人化的书,作者是一位年轻的美国学者,她本人就是苏联晚期俄罗斯犹太移民的孩子。(20世纪90年代,吉尔伯德和我一起在芝加哥大学学习,她现在在那里教苏联历史。)她的书和电影《再见列宁》中苏联/共产主义的怀旧风格一样。但这个主题不是苏联本身,而是对西方的愿景,这一西方文化的光环吸引了后来的几代苏联人。潜在的怀旧情绪是因为苏联社会极其看重文化(包括但不仅仅是西方文化),并培养了强烈的集体情感。
读了这本书,我不禁为苏联的宣传者感到遗憾,他们为让公民爱上苏联社会主义而辛勤工作了这么久。要是他们读了一点资本主义营销理论,并掌握了物以稀为贵的思想就好了。苏联宣传者与他们实现使命的机会失之交臂,只有在苏联解体、宣传部门被西式广告和公关人员取代之后,才出现了对苏联社会的怀旧情绪。
本文原载于《伦敦书评》,作者希拉·菲茨帕特里克正在完成一本关于二战后俄罗斯移民的书,并开始撰写列宁的妻子娜德日达·克鲁斯卡娅的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