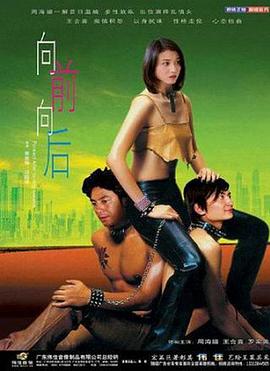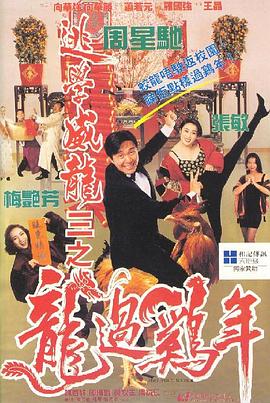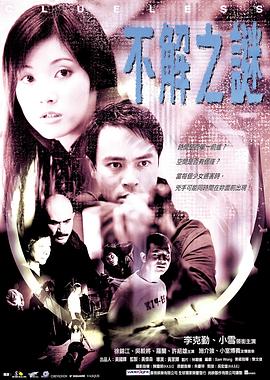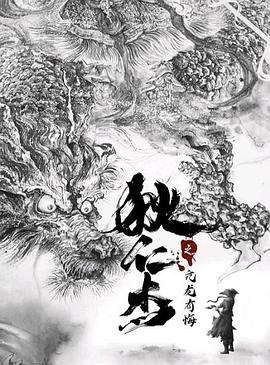剧情介绍
这是一部关于记忆的小说,这是一部讲述抵抗遗忘的小说,这更是一部试图解读生命存在与虚无的小说。在这部小说中,故事的呈现打破了时间界限,也许作者有着文本上的考虑,但也许这样的排列更符合记忆之于存在的真相:碎片性、偶然性和荒诞性。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艰难而又缓慢地打捞记忆,然后重新进行梳理,把那些他所经历过的事、爱过的人、做过的梦,重新组合,打破时间的线性顺序,以1995年为起点,用向前和向后两个时间维度的讲述,为我们构筑了一个个似真如幻的场景。两个方向的线索,相互独立,又相互印证。
既然不想忘却,那就拼命地回忆。
(《二十九》)这样的句子即便不能说是入木三分,已足以让读者的眼睛饱含热泪!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着自己的故事,我们就是自己的故事的主角。我们以为记忆就在每天扑面而来的时间里,以为就在我们走过的每一个脚印中,以为就在我们说过的每一句话中……许多我们以为早已刻骨铭心、永远不会忘记的记忆,在时光的流转中逐渐被每天堆积的琐碎事件所遮蔽,假若不用心去找寻和分类梳理,也许就再也难以找回。而作为一个在这个世界上来过一回的生命,假若没有了记忆,我们还剩下什么是属于自己的?不想忘记,是因为我们必须通过记忆来印证生命的存在,并以此证明,我们在这个世上来过!在小说的最后,作者用了六个“我喜欢……”的句式,近乎固执地写下了自己记忆中最纯净、最美的画面。如同音乐的婉转回旋,仿佛是为了重复印证记忆的“永在”,其实是对于记忆终将消失的绝望的呼喊!
关键词:父亲,我
写作,从某种角度上讲,其实就是人对于自身的一种探索。从古希腊柏拉图的“做你的事和认识你自己”、蒙田的“我一心思想我自己”、卢梭的“首先要充分认识你自己”,到尼采的“成为你自己”,都是为了求证“我”的存在及价值。
“我”与“父亲”的关系决定了这部小说的基调:压抑、孤独、抗争——“父亲”意味着专制,而“单身宿舍”其实就是一个隐喻,隐含着对自由的渴求、青春期的骚动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和自身的孤独。卓亦雄与父亲的抗争,就是对专制的反抗和对自由的追求。
在逃脱父亲的势力范围之后,“骆驼、张三、罗新,或者是同住一栋宿舍楼的童刚、汉成”(《二》)成为他构建的“自由王国”的重要元素。但“众神欢宴之后,留下来的只有孤零零的我。”(《二》)那么,孤独是一种宿命?——也许,在父亲看来,儿子就是一张白纸,任由自己描绘、涂抹。但青春期的卓亦雄却感到无法容忍父亲的粗暴方式,他选择了以“离家出走”的方式进行抗争。
关键词:爱情
爱情是什么?这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却越来越令人难以回答。当人们为“爱情”这个神圣的词批上“荷尔蒙”的注脚时,爱情已被世俗的笔涂抹得面目全非、丑陋不堪。
所以才有了文学。
卓亦雄的爱情大致分为三种:爱、互爱、被爱。对米雪的感情属于第一种“爱”,是主动奉献、不求回报(或“没有回报”)的感情。与若英的感情是互爱,即是互有纠葛、相互缠绕的爱,是最理想的情感的状态。与青峰和小鱼的爱,应划入被爱的范畴。虽然他曾努力经营与小鱼的情感天地,对青峰心怀愧疚,但总体来说,他们之间的感情,被动接受的成分远远大于给予。
“不知不觉中,我们的活动项目悄然发生了改变。闪烁的霓虹,缠绵的音乐,挤进了每一个平凡的夜晚。”请女孩跳舞,在跳舞中搞一些小动作,对舞场上的女孩评头论足,似乎都可以被解读为“荷尔蒙”旺盛的象征。朋友“循循善诱”,卓亦雄却心不在焉。因为,他知道,这些都不是爱情。在他的的心中,还有着对于爱情的渴望。
“……你还和班上哪个同学有联系?”我沉默了片刻,突然想起了若英,而我的回答却是:“都没什么联系了,只有吕宁有时候来红都商场找我,就是那个从江苏转学过来的吕宁。”(《三》)——这段对话很短促,之后也没有刻意渲染。但却展现了作者对于爱情的态度:绝不轻易碰触。
虽然同在一个小城,虽然西门邮局就在我们学校附近,我和若英还是频繁地通信。有时,我还会在信封上俏皮地注明‘十万火急’或者画上一根鸡毛。有一次,我收到若英寄来的一枚绿叶而诗兴大发,立即写了一篇简短的散文诗。大意好像是把那枚绿叶比喻成人生之帆,期待乘风破浪。
(《附三》)在信仰丧失、实用主义至上的年代,且在前途未卜的情况下,年轻的心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心理、精神上的)。然而最大的苦难却是把“自甘堕落”当作世俗至上的“明智”。卓亦雄的迷惘在于:他精神上的“洁癖”遭遇了现实的泥潭,并且在泥潭之中努力守卫心中“爱情”的净土。
走在黑漆漆的山路上,我才大着胆子悄悄牵住了若英的手。为了掩饰内心的激动,我目视前方,嘴里还在不停地介绍附近的情况。若英仿佛没有感到我的那只僵硬的手掌,回应着我的话题。(《附五》)我记得自己伸出手臂怪异地搭在窗沿边,犹豫着能不能搂住若英的肩膀。动作无比别扭,心里面有一只小鹿,咚咚跳动。若英说,你的手不累啊,我说是有点累,傻呵呵地就顺势搭在她柔软的肩上。(《附六》)——这两个细节描写了初涉爱河的情人间的一个小场景。简单的几句描写,惟妙惟俏地勾画出了主人公的心理历程。作者对于爱情态度和进退维谷、患得患失的心理跃然纸上。
在这部小说中,除了一再隐现的“孤独”的主调,还有一个重要的符号:写给米雪的14页的情书(《十一》)。他甚至不敢直接落上自己的名字,而是将名字以一种隐秘的方式留在信封里面。与其说是卓亦雄与米雪的爱情,还不如说是卓亦雄的单恋。
卓亦雄的心为之几近痴迷的状态,而我们看到的结果是,米雪始终若即若离,毫无交结。这就注定了这场“意外”的爱情只能給卓亦雄的人生增添一段迷乱的记忆。
与米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若英。若英与卓亦雄的情感有交结、有期盼。种种迹象表明,她十分愿意卓亦雄进入到她的生活圈。然而,“我和若英在花溪公园漫步,也许是上苍要满足我的愿望,我惊奇地见到了一道熟悉的风景,小桥流水青山,这不就是米雪给我的那张照片上的景致吗。”卓亦雄所想的却是“我没有想过实现这个愿望会如此容易。站在米雪曾经留影的位置,我呼吸着她残留的气息,当然这个想法又一次脱离了现实。我假装沉浸在美景之中,久久不愿离去……”(《十八》)不禁想起那句名言:爱情,就是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遇到合适的人。反之,在不合适的时间不合适的地点遇到不合适的人,这种错位就一定会导致荒谬和悲哀。
透过小说的讲述,可以清晰地看出,作者对于错位的爱情有着清醒的认识,也正是由于这种认识的清醒与真实,才使得小说带给人的绝望、荒诞感更加深透骨髓。
关键词:孤独
在哲学文化范畴内,“孤独”是一个取之不竭的疆域;在技术文本上,它则充当了复杂的隐喻:努力读书、写情书、恋爱、奋斗……作者通过对记忆的追述,为我们绘出了一幅幅有关青春迷惘、苦闷、冥思、剖析的画面,借此展现生命的冲突及主人公鲜为人知的一面。
写作,成了卓亦雄抵抗孤独的武器。在反复隐现的“孤独”的旋律中,有关人生、存在的调色板获得了空前的丰富。
在卓亦雄看来,人是绝对的孤独,而欢乐则是相对、短暂的。基于对人的这一处境的基本认识,才能够坦然地应对生活中不断遇到的尴尬、困境。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孤独”不是作为主要素材处理的,而是被当作一个不断隐现的旋律,不时地悄然奏响,如同背景音乐一般,贯穿整部小说。
因为孤独,“我”选择了写作:很多人说,文学是孤独的,而我的感觉却恰恰相反,它是我抵抗孤独的武器,调动身体里全部的意志,一点一点擦拭时间覆盖的灰尘,我也一次次靠近和抵达内心的秘境。诗歌由此主导着我的日常生活,不论白天还是夜晚,我可以在任何时间写作,包括睡梦之中。我准备了纸和笔放在枕边,就是为了抓住稍纵即逝的灵感。(《二》)在这种语境下,“我准备了纸和笔放在枕边,就是为了抓住稍纵即逝的灵感”,这个动作其实就变成了随时随地准备抵抗孤独的隐喻。
在十九节里,作者提到了“理想国”:“我确信,每个人的内心都存在一个‘理想国’。那里的天空发出柔和的、幽蓝的光,飘逸令人心安的气味。草地一直延伸,无边无际,它完全根据某种想象,进行快速的构造。没有逻辑束缚,不需要理由,一个深夜不眠的人,从一个瞬间跳跃到另一个瞬间,寻找丢失的快乐和痛苦,如同黑夜为我布置的一项永久性工作。”而他的理想是“用手中的笔谋生,把兴趣、爱好当做自己的职业,这样既可以在工作中享受快乐,又可以把工作当成兴趣、爱好。”但却不得接受做一名“烟工”的现实安排。
卓亦雄在烟厂的工作始终是孤独的。
表面看来,是因为他无法融入“烟工”们造成的,但实质上,是源于他无法认同自己的“烟工”身份。这种现实与理想的分裂,像一团阴云一样在字里行间飘荡。
阅读、写作成了他实现弥补这种分裂的手段。每取得一点成绩,他就感到自己向理想靠近了一点。这种喜悦,他需要与人分享。于是,“每当有朋友去找我玩,我便会翻出最近发表的文章,给他们看,向他们展示,或者说炫耀,这是虚荣心在作怪。随着发表数量的增多,也许朋友们的回应没有预想的强烈,我才停止了这种行为。”———无处分享,使得他更加感到孤独!在该节的附文中,作者写到他儿时的“初恋”对象米雪,写到“拉练”:“高年级学生唱的歌曲至今回荡在耳边: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哦!哦!哦!哦!芝麻开门!芝麻开门!……”这样的安排颇有深意:与成年后的孤独相比,童年的欢乐变得弥足珍贵。
关键词:八十年代
作者写作这部小说,最初拟定的副题是《一个七十年代生人的生活副本》,小说的主体背景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
八十年代中期有两首歌风靡全国,一是电视剧《霍元甲》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一是香港歌星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用现在的说法就是,都是正能量的。
如今,唱着这些歌曲成长起来的我们已经不再年轻。有时偶尓哼唱起来,熟悉的旋律依然能够让我们回忆起当初的激情。
后来,一些关于爱情的流行歌曲逐渐多了起来,比较简单、直接,一改传统含蓄、优美、委婉的风气,但因为迎合了当时“开放”的思潮,一发而不可收拾。
朋友们笑谈:以往的情歌,是从“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端端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绕了一大圈,最后才过渡到“张家溜溜的大哥,看上溜溜的她哟”,而且还要以“月亮弯弯,康定溜溜的城哟”来遮掩爱情的表达。但后来的情歌,直接变成了一种声嘶力竭的吼叫:“对你爱,爱,爱不完……”本节还写到了“商场”。在我们这一代人看来,这个名词还承载着时代文化记忆:——以八十年代一个小孩的视角看来,霓虹闪烁代表着大都市的繁荣街景。红都商场的霓虹灯在黑漆漆的街道上,显得格外不同,透出一股时尚气息。而走进亮如白昼的商场,亮铮铮的钛合金柜台比起百货大楼的木制柜台洋气许多。(《六》)八十年代,很多小县城都经历了“百货大楼”时代和“商场”时代。商场作为那个年代的“新秀”,迅速取代了百货大楼。“百货 大楼”是计划经济条件下保障百姓日常生活所需的一个机构,而“商场”本身就是官方为“市场经济”量身打造的一个商业场所,它具有新生事物的后发优势和政策优势。在我的记忆中,自从有了“商场”之后,“百货大楼”就渐渐开始日渐衰落。
“百货大楼”的衰落,暗示着一个时代终结。许多时候,人都会沉迷于某种记忆而不能自拔。比如,关于爱情,关于商场、邮局、衰落的百货大楼……其实,记忆与梦幻具有相同的性质:美好,但是遥不可及。
关键词:记忆
在这个物质世界里,我们需要为自己的心灵找寻到可以皈依的家园。回忆或者憧憬、反思或者剖析,就是通往皈依的台阶。
写作中“皈依”作为一种精神指向,也许与宗教无关,但一定具有宗教般的神圣和庄严。
很久很久以后,我们会不会想起很久很久以前……(《附十》)——卓亦雄不经意间道出了内心的忧伤和迷惘。
这句话,让数十年后的我们感到,记忆的匣子一下子被打开,里面还存放着我们的青春、梦想、快乐、忧伤……这是我们共同的记忆。即便,卓亦雄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是在一个充满喜剧性的场合,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句箴言。如果说写作是写作者自我内心的一种需要,但这句箴言,通过一系列情节的铺垫,自然而然成为读者情感的引爆器:我们听到了一个声音——一个来自我们自己内心的声音:关于彼时,你还记得多少?现实太过沉重,也太过琐碎。而“回忆”给了我们一个恰到好处的距离,它成了我们对时间、生命以及自身的一种理解方式。
关键词:下岗
“下岗”作为一个时代的热词,在文学中至少可以成为一种隐喻,有很多故事可以写。但作者只是一笔带过,仿佛是吃饱饭之后随意将碗放下了。事实上,确实是吃饱后放下的饭碗,所以饱餐之后的人在放下的时候也并不在意。但这只碗却再也找不回来了……职工大会上,刘经理用报纸上的一篇新闻报道作为开场白,其间贯穿了“国家宏观调控、改革转型、抓大放小、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等等词汇。(《十四》)——这段话的排列很有意思,由于文学对于政治话题的失语,沉重的话题被貌似超脱的调侃掩盖了。
没有选择的权利,必须接受,现实残酷的一面展露无遗。《十四》)——通过这段话,几乎可以认定,“轻描淡写”一定是作者刻意为之。
下岗,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就业制度在经济转轨的产物。与之相对应的是,作者在附文里讲述了几个少年时的游戏:翻墙、走钢管,其间还顺带讲述了找鸡菜和倒尿罐的关于“面子”的“屈辱”的记忆,以及“最为气派的厕所”里的荒谬的小插曲,这些都是“我”不愿意接受却又只能接受的现实。与“下岗”形成了一种隐形的呼应!铜仁、地质大院,我们在这里成长,在这里恋爱、生活,在这里痛苦、欢乐。它已非地理层面的个体故乡,而是铜仁70后一代人的精神家园。它带着一个人难以放弃的独特个人体验,却又烙上了一代人共同的生命历程印记,是一代人的精神史和生存史。即便是读书、恋爱、上班、下岗……我们爱着,也被爱着;我们伤害着爱我们的人,同时承受着命运对我们的伤害——作者以忧伤的文字为我们留住并展示了这一切。
但是对最重要的、与生存有关的伤害,我们却又只能保持缄默……
我们看到,在小说中,记忆总是以其个人化又极具现场感的方式呈现出来,作者对任何事情背后的荒谬都不做深究。这种超然豁达的胸襟和满怀爱意,佛家叫做“慈悲为怀”。通过这种极具悲悯情怀的回忆,把小城的冷暖、时光的冷峻和命运的荒谬多舛呈现出来。
所以,回忆便有了与心灵契合的力量。
关键词:宿命
“偌大的操场,我总能够不偏不倚地撞到篮球架上。越想避开越是撞……”(《附二十四》)类似带有暗示或者隐喻的语言并不少见!严密的逻辑推理有可能发现真理,但人对命运的感悟,往往要依赖直觉。卓亦雄依靠自身的直觉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生就是各种意外的串联!”(《二十四》)人在最艰难的时候,除了坚持自己的理想,也需要白日梦。这样说起来,似乎很荒诞。我们在回顾自己的人生之路时,常常会发现这样那样的谬误,总觉得若能再做一次选择,自己的人生将会是另一重景象。
我们常常感叹时光易逝、命运多舛,殊不知,宿命的篮球架一直就等在那里,而我们,无论怎么折腾,总会准确地撞上去……小鱼本来是要介绍给张三做女朋友的,阴差阳错地与卓亦雄“撞”上了——“耳朵是被板凳砸的,一个月之后我的耳朵好了,小鱼也住进了我的心里。”在青峰心里,早已把卓亦雄当作情感的港湾,因此,“在铜仁的街头巷尾细心地看招聘广告,像一只准备筑巢的燕子”(《二十四》),但却只能与他擦肩而过……这就是卓亦雄的“宿命”。
关于小说及语言
作者为我们构筑了一座城,这座城的名称就叫“青春”,由几个具有象征意味的人和物构成:“父亲”象征着权威,是卓亦雄要全力反抗的对象;若英象征着诗歌和未完成的关于爱情的美好梦想;单身宿舍象征着青春的据点,是他青春出征和归来疗伤的地方;舞厅象征着世俗的狂欢……这样划分也许不一定妥当。但事实上,一部好小说需要我们以俯视一座建筑设计图的眼光,思路才能更清晰,才能准确判断出各色人物在里面的活动。因为,小说中的每一个故事或者人物,他们相互间都是孤立的,而且往往是片面的。这时,就需要我们选择一个更高的“点”来看,只有这样,才能拨开层层迷雾,看清作者的真实意图。
整部小说弥漫着的忧伤、迷惘和孤独气息挥之不去,但却并非作者刻意为之。他只是缓慢地讲述着自己的故事,并一直努力在适当之处嘎然而止,重新开始讲述另一个故事,力求以这种讲述方式预防自己的情绪走入一种极端境地。恰恰是这种努力,让我们更深地感觉到了他内心的挣扎。
出于生存需要,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阅读很多文字,比如广告、新闻、家用电器使用说明书……这些文字,指向明确、定义清晰,完全是实用的文字。但这些文字都缺乏诗意。
诗意提升了人类的精神品质,但从“实用”的角度看,却又“百无一用”。所以,诗是脆弱的,也因此而弥足珍贵。相比于诗歌这种艺术形式的自由和狂放,在小说叙述和日常生活中获取诗意则更难。尹嘉雄对于“诗意”的坚持使他的小说站在了一个较高的层面上。
回忆体小说之难,难在对虚实的把握上。创作,从根上讲,笔下千万言,其实写的都是自己。当然,这是对敢于直面自己的写作者而言。因为,他们是用自己的生命在写作。至于那些靠编故事,以题材、情节取胜的码字工,则另当别论。
从文本上看,小说的语言干净、简洁中透出一种优雅;故事的叙述清晰而又克制,如同主人公的内心,情感丰富却又能把握分寸。这既需要对小说语言的把握能力,也需要相当强的对自己内心的控制能力。
不记得是谁曾经说过,审美需要距离。小说的叙述角度、语言的密度其实也是构成“距离”的重要要素。小说视角向内,有助于让读者能尽快进入作者设计的情节,同时也留下了更多的空白。尹嘉雄的小说语言分寸感拿捏得恰到好处,能充分调动读者的想象力,以弥补文字叙述留下的巨大的空白。
音乐、绘画、书法等艺术都讲究“留白”,对于小说艺术来说,更是如此。
对于小说创作来说,“缓缓道来”需要一种气度。不卑不亢的叙述,要求作者对于小说的整体构建、节奏要有较强掌控能力。 他的讲述,清晰而又恍惚,沉重却又轻盈。读累了,就让眼睛休息一下,让自己回到现实的生活中,看看周围的事物,或者去看看山、看看水。再回到小说中来,又感到之前的阅读似乎意犹未尽,于是再回过头来反复读,再获得与之前不同的感受。
好的文字是值得反复读的。一个好的讲述者,往往善于营造一个强大的气场。
你进来,就进入了这个“场”;你出去,“场”的气韵依然在胸。
“向前向后”,这个标题就给人一种飘忽感,让人随着作者的讲述在不同时空飘来飘去。这种飘忽不是在儿童乐园乘坐海盗船的大起大落(那其实是拙劣的讲述者常用的方式,以强大的推动力造成生理上的紧张感),而是坐在后花园中的摇椅上 来回晃荡。来去、起落之间,会让你产生灵魂出窍的感觉,然后,与自己的青春、梦想、爱情相遇……在写法上,作者首先着眼于那个年代,设计出整部小说的构架,然后再离析它,写好那些带有关键性质的细节:离家出走、舞厅、同城情书、对爱情的揣摩、考工作等等,做到脉络清晰,气定神闲,纷繁中见条理。让我们感受到了他对文本驾轻就熟的能力。
“如果可以,我想按下重播键,一切从头上演一遍。最好是直接穿越到锅炉房的门口,在锅炉排放的一大片白茫茫暖烘烘的蒸气中,再次欢呼雀跃,想象着自己腾云驾雾。”(《十六》)作者向我们展示他的一个狂想:他要自由地穿梭于过去和现在之间,并且将痛苦和欢乐重新进行分配。 不论是恋爱,还是童年快乐的生活,反思的意味始终在文字中游荡。也许,他还怀着更大的野心:在时间的坐标上,将每一个细节都进行精雕细琢。
事实上,对一部好的小说,任何理论都是苍白的。《向前向后》没有波澜壮阔的场景、跌宕起伏的情节,但作者以素描的手法为我们展现了那个时代铜仁人的生活和精神状况,截取了一个与青春、与爱有关的生活断面。最重要的是,在书写中坚持诗性原则和对小说形式的探索精神,足以弥补情节的平缓留下的缺憾。
“向前向后”不是空间的指向,而是作者心中的时间的座标。作者写下了对时间的疲惫、失望和伤感。所以,也可以把这部小说视为对于青春、爱情、记忆的祭奠。
淋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