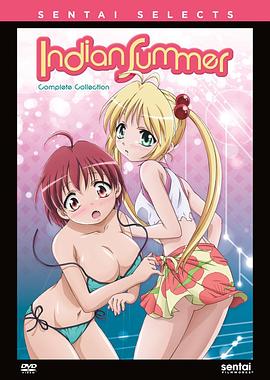剧情介绍
天涯微信号:tyzz1996
天有际,思无涯。
投稿邮箱:tianyazazhi@126.com
点击封面,购买本期杂志
宝庆路三号:当樱桃变成玉兰
汗漫
1
宝庆路两端生发出常熟路(向北,至静安寺)、衡山路(向南,至徐家汇),与淮海路或者说民国时期的霞飞路相交叉,形成上海的一个十字街头。
宝庆路三号处于此地,由五座德式建筑风格的小楼、六千平方米的草坪构成的私人庭院,名震上海滩——早年,仆人来开门,需要骑自行车从小楼方向迤逦而至。后来,庭院的栖息者、水粉画家、音乐鉴赏家、文学爱好者、老克勒、本文主人公徐元章,在没有仆人的年代里,亲自骑自行车来开门,迎接另一个老克勒或者年轻女子,喝咖啡、跳舞、画画、听唱片、闲话、调情、私语、发呆……
《十字街头》剧照。
在街头,我偶尔会想起上海明星影业公司一九三七年出品的黑白电影《十字街头》。赵丹、白杨主演。如果是春天,百花香,太阳暖和地照着我不算破的旧衣裳,就更容易想起这一电影中的插曲。每个时代都在追问着每个人的选择,在露天与内心双重的十字街头,红灯问罢绿灯亮,也不一定能遇到一个好姑娘。
我多次穿过一系列十字街头,访问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宝庆路三号。大门黑色,紧闭。院子内偶尔有犬吠。沿街一侧被竹编篱笆细密封锁,某个角落处曾经有旧漏洞被新竹子填补——一个同事、朋友,刘先生,上世纪七十年代在这庭院内某一小楼改建成的小学校里读书三年,屡屡从这一漏洞中进出,感觉像在语文作业中的一个括号内填词、改病句。“小学旁边两栋楼被改成派出所,警察进进出出。小学、派出所之外,还剩下两栋楼,被一道纱网隔出去,成为徐家人生活的小天地。没有从前阔气了,但能有这样一个安闲的角落,在那样的年代,也稀少啊。我们同学常常趴在纱网上,偷偷看徐元章和他女朋友在草地上读书、喝茶——那场景,真像一幅俄罗斯油画。”
早年,一九四九年以前,大门一侧曾经有两个信箱,分别写着“周”“徐”二字。
“周”,指这一院落的主人周宗良:宁波人,牧师的儿子,由学徒开始在上海滩闯荡,最终成为了德国染料业在华的总买办,所建立的商业分支机构遍及内陆各大城市,并进入染料业以外的投资领域:地产业、金融业、轮船业、纺织业……曾经担任民国时期的中国银行董事、中央银行理事等职。一九四八年去香港定居,所携财富装满两架飞机,在香港富豪排行榜上居于第二位。一九五七年病逝。
“徐”,指周宗良的女婿徐兴业:初为家庭教师,后成为四小姐周润琴的夫婿。周宗良出走香港后,这一庭院的主人成为徐兴业。一九五七年,周润琴赴香港参加父亲葬礼后,赴法国游历一去不归,初有信件往来,后无消息,失踪,导致其儿子、周宗良的外孙徐元章,在多年后与其他周氏子孙发生房产继承权纠纷中失势。徐兴业后来任职于某出版社,业余写作,长篇小说《金瓯缺》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荣誉奖,一九九○年去世,避开了儿子将要去面对的遗产纷争。
现在,门侧的信箱一个也没有了。徐元章也在二○○七年周家子孙产权纠纷发生后不久、法院勒令其搬出宝庆路三号以后,没了音讯,直到二○一四年去世,在媒体中重新成为一个短暂话题,让上海滩最后一批老克勒伤感、念叨一阵。目前价值数亿元的这一庭院,已经有了身份不明的新主人。院子内有犬吠,已经不是徐元章的宠物在呼叫了。
“忘记某人就像忘记关掉院子里的灯,/于是它整天亮着:但那也意味着回忆/——因为那光。”(阿米亥)宝庆路三号庭院里的光,用灯泡形状的头颅,在回忆?
2
刘先生一直住在宝庆路附近弄堂里,请我去他家旁边的咖啡馆喝咖啡,聊起我们两个都感兴趣的徐元章。
“他长相一般,有女孩子味,眼神湿漉漉的。初中没毕业就不上学了,在我们弄堂工厂里糊纸盒,和我哥是工友——一个少爷,纸盒也糊不好,就给大家讲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三个火枪手》《三国演义》……讲得生动,像说书人,到关键情节处就卖卖关子、吊吊胃口。大姐大妈们替他糊纸盒,还带吃的、喝的,宠着他。他家藏着不少书,我去借书,他犹豫半天,怕书丢了、被人告发了,最后决定让我坐在他家窗台下看书,看一个下午。天暗了,我才恋恋不舍回家。第二天再去他家接着读。那半面墙的书柜啊,竟然一直没有散失,真是奇迹。我读小说,徐元章一边听降低了音量的贝多芬啊、肖邦啊,一边画水粉画。偶尔抬眼问我:看到姑妈出现的那一段落了吗?注意那一段啊……”
在弄堂工厂里没干多久,徐元章就回了家,不上班了,全心全意在门前草地上谈恋爱——表演俄罗斯油画一般的异国情调。门外,宝庆路附近的十字街头,的确有俄罗斯侨民们在二十世纪初流浪上海后建立的东正教教堂、普希金雕像。淮海路上反复走过锣鼓喧天的游行队伍,但徐元章不关心这些,他只关心爱情,除非爱情不再关心他。最终,他娶了那个有德国血统的美女。若干年后,这女子像徐元章母亲一样带着孩子出国,同样渺无音讯。一个异常美丽的庭院,让其中的亲情和爱都显得异常——触目的美,必然带来惊心的痛?
“那女子很贵气,一看就不是徐元章能驾驭的人。旧公子,有情调,收藏了很多老唱片,没钱。他靠卖画、做美术教师有一些收入,但要花大价钱养护这园子。到电台讲过古典音乐。朋友们也给他一些接济。他没有什么新衣,总是穿着从前的衣服,吊带裤、尖头皮鞋,皮鞋上有裂纹。徐元章啊,只适合与那些浪漫主义小姑娘谈谈艺术,悄悄亲热亲热。”
“你说的‘谈谈’和‘悄悄’,像在总结自己的人生经验吧?”我这样调侃,刘先生嘿嘿地笑。
3
徐元章只画上海滩异国情调的各种建筑,这自然与宝庆路三号内的生活遭际有关。
像桃花源一样可以避世,德式风格,用的是从法国进口的美国材料——外公周宗良对宝庆路三号的构思与建设,历时七年。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滩,这一庭院异常醒目,被觊觎——日伪时期上海汉奸行动队队长吴世宝,屡屡以“私通重庆”罪名相逼,并筹谋绑票,以图获得这一院落。
周宗良每每外出,都由四五个保镖左右观察、前后卫护,小心翼翼推开那扇黑色大门。他的手杖,其实是一把暗藏锋芒的剑。即便如此,其妻仍旧被夺门而入的蒙面者绑架,后以巨款赎回。周宗良,不是魏晋人士,也不是陶渊明,他知道自己所处时代的危急和紧迫。
一个颜料商人的后代,用颜料、色彩来表达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吧——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徐元章在上海画界逐渐成名。
那个年代,一个画建筑的人,必然与上层建筑发生关联——淮海路、汾阳路、岳阳路上,几幅领袖像的绘制者当中,有徐元章、陈丹青等等当时上海画坛的青年才俊。“站在高高的梯子上,画整面墙。这颧骨上的一点,是最后一笔,也是最难的一笔——全画最亮的一点,用白颜料,要点得精准,就必须在一米外仔细端详,然后啪一声,点上去,顿然生辉。”多年后,他在某部纪录片里回忆这一往事,表情有些失神、走神。
纪录片拍于二○○七年的遗产纠纷案发生之际。徐元章想通过这部片子影响舆论,从而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判决。他大概也想通过这一片子,让失踪于异国的母亲和妻子,看到一个进入晚景的儿子、丈夫的无助与孤独?否则,他不会让记者、录音笔、照相机、摄像机一类外界事物,侵入宝庆路三号这一高尚的院落。
4
五个独立的两层别墅分布于花园四周,最初分别为:主人起居室、会客室及餐厅,子女、家庭教师及来宾起居室、仆人起居室及配电室——把功能分解于有距离的不同别墅,确保不同层级人物的私密性。“文革”后,弄堂小学和派出所搬出,宝庆路三号完全回归徐家或者说周家。
“我小舅舅骑着马,在草坪上练习盛装舞步,周围是一群名犬。女子们围着看的时候,他在马背上的样子显得更高傲、更英俊。你看,当年他们烧烤的铁架子还在。生锈了。我一个人是不会在草地上烧烤的,显得滑稽啊。我爸爸当年进入这个院子当家庭教师,就在那一座楼里给我妈妈讲课,妈妈当时是高中生,师生恋呵呵。”徐元章在纪录片中笑了,面对镜头,像面对一个虚无的母亲和爱人,眼神有些羞涩、自得和惆怅。镜头移动,他身旁门框上似乎有白蚁蠢蠢欲动。
一群老克勒每周日下午三点,在“会客室及餐厅”所在的那一座楼里聚会。所谓“克勒”,有两种解释,一种是“class”——阶级、阶层、台阶;另一种是“colour”——花朵、花花公子。一种有花花公子气质、花朵气质的旧贵族人士,年龄跨度在五十余岁到八十岁之间。其中,有昔日钢铁大王的孙子、船王的孙女、面粉大王的外孙、火柴大王的侄孙、晚清重臣的后人……这样的聚会,像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一条索引、一个脚注。
老克勒们穿紧身西服或燕尾服,头发精心染黑,发膏和尖头皮鞋在一个人身体的上下两端,闪闪发亮。即便在室内、在复杂造型的吊灯下,他们依旧戴着可变色的墨镜,以便掩盖眼角皱纹。喝手磨咖啡,品红酒,用英语或精致的沪语回忆往事。他们甚至不说“阿拉”,而说“吾伊”。显然,“我”“俺”一类普通话、土话,无法敲开这扇黑色大门。需要语言、妆容、服饰来加固某种尊严和存在感。
在纪录片中,看到一个打扮成“猫王”形象的八十岁左右的老人,他应该经历过三十年代。七十岁以下的老克勒,比如徐元章,更多是在追忆旧时代的光影气息——从父辈那里,从老照片、老电影里,从血液里。《胡桃夹子》的音乐响起,老人们拥着美艳女子翩翩起舞。地板有细微裂纹、墙纸陈旧剥落的巨大舞厅,顿然辉煌。徐元章很少跳舞,像一台戏剧的编剧、导演、制作人、剧务,站在墙角微笑、观察,随时为大家斟酒、续茶。从舞会这个角度,一个老人眺望着早年的美景良辰。
或许由于怀抱中的女子过于诱人,那“猫王”滑倒在地了,顺势做出天鹅之死的动作来自嘲:“心爱的人啊,我为你而死。”哄堂大笑。
出现在这一院落、这一舞厅里的女子,大都是上海艺术院校里的学生,被某一老克勒带进这圈子,也就有了关于上流社会的谈资。她们会拜徐元章为师,学水粉画,在大草坪上面对这五座别墅,表达幻想和心动。大部分时间,这些位于花园南侧的建筑处于逆光状态,画家就要学会辨别、呈现出阴影的层次和深意。纪录片中的场景:徐元章与一个女孩手拉手在暮色里站着,女孩几乎依偎在他怀抱里了,白玉兰树的影子在窗子上随风晃动……
记者询问与女孩相处时的内心感受,徐元章回答:“我老了,对于她们的爱是干净的、安全的、可以信赖的。”还算是一种比较体面的回答。
对于越来越多的造访者,试图进入这一圈子的陌生人,徐元章在抗拒:“那个某某,真是拎不清,带来一个外地女孩——我这种地方是外地人能进来的?再漂亮也不稀罕的。上海小姑娘嘛,自然是欢喜的、欢迎的啦。”这段话让我想到契诃夫,想到他最后一部作品、话剧《樱桃园》。
宝庆路三号,像某个隐形的契诃夫写出来的一部戏剧,真实而又虚幻。
不同的是,在这一戏剧里,俄罗斯的樱桃变成了上海的玉兰。
5
《樱桃园》剧情梗概:
十九世纪末,俄国贵族阶层崩溃,新兴资产阶级咄咄逼人,像长期寂静的樱桃园附近突然出现的火车站、火车那样,咄咄逼人。女主人公柳苞芙,在丈夫酗酒而死后,为新爱情而移居巴黎、耗尽财产,归来,不得不拍卖掉世代居住、寄予无限情感的樱桃园。而樱桃园的接手者居然是柳苞芙家族昔日奴隶之子罗伯兴。剧中,拍卖日的前夜,樱桃园里还在举行舞会,但舞者阵容已经不整齐了:商人、家庭教师、女仆、火车站站长。八十七岁的老仆人费尔斯,站在舞厅一角很不愉快地嘟囔:“早年间,我们这里跳舞的都是些将军啦,男爵啦,海军上将啦。现在却请来了邮局职员和火车司机。他们还摆好大的架子呢。”
徐元章像《樱桃园》中的谁呢?像柳苞芙、柳苞芙的女儿安妮雅、费尔斯等等人物的混合体,尊贵与卑微、前欢与新愁的混合体——宝庆路三号,只有他一个人在演出。连宠物狗这一道具,也蜕化为一只普通家犬。他必须分饰各种角色,直到曲终人散,只剩下玉兰树兀自开开落落。但他显然不像剧中的商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罗伯兴,也不像冷眼旁观这一切的大学生特罗菲耶夫。
罗伯兴在感慨、愤懑:“和你们混在一起整天不干正经事,可把我害苦了。我不能没有事干,我不知道怎么来安顿这两只手;它们闲着晃动的时候,像别人的手。春天里我种了一千亩罂粟,现在净赚四万卢布。当我的罂粟开放的时候,那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图画啊——特罗菲耶夫,你为什么那么骄傲?”
特罗菲耶夫在沉思、抒情:“你父亲是奴隶、庄稼汉,我父亲是药剂师,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你就是给我二十万我也不要。我是个自由人。你们,无论穷人还是富人看得很重的东西,对我来说就像是天空里的飞絮,对我产生不了影响。我有力量也很自豪。人类在走向崇高的真理,向可能存在的幸福进发,而我置身于这队伍的最前列——我能达到,我自己能达到,或是向别人指出达到目标的道路。诸位,上马车吧……是时候了!火车就要进站。”
在这句话的结尾处,传来砍伐樱桃树的斧声和火车的汽笛声。
话剧《樱桃园》初次进入中国舞台,是在二○一六年,徐晓钟、林兆华先后导演,濮存昕等演员演出。熟悉外国文学的徐元章,是否读过《樱桃园》这一剧本?估计他不会喜欢契诃夫的主题:我们都是要告别樱桃园和旧生活的人,不论是根深叶茂的贵族,还是草间求活的平民——车站已经修到了门前、胸前,一个人必须接受新世界的进入与拷问。就像必须接受宝庆路三号黑色铁门外种种的人物与事件,突然进入并拷问。而我们,如何守住内心深处的樱桃树与灯火?
二○○七年,周宗良居于海内外的二十三位子孙,就宝庆路三号产权起诉徐元章,要求分割遗产。法院鉴于徐元章母亲下落不明,继承链条中断,故判决“徐元章与本遗产分割案”无关,勒令其搬出花园。徐元章为这一诉讼而改变高冷风格,频频出现于电视台“心灵花园”一类痛说悲诉、暴露隐私的娱乐节目,为自己申辩——意料之外,但也在情理之中。无奈、无效。
一个水粉画家在宝庆路三号消失,最终在人间也消失了。新贵们在拍卖场举牌,赢得这一花园中的草地和玉兰。
6
契诃夫对商人罗伯兴并非简单鄙视,而是充满同情与理解。
其实,他对笔下人物都带着同情与理解,像作为“契诃夫诊所”的主治医生面对病人那样,全身心地感受着他们的剧痛和隐痛——小说史就是疾病史。
契诃夫最喜欢的人物,应该是那一个总也没有毕业、被樱桃园女主人柳苞芙讥讽“得了洁癖、怪人、连恋爱滋味都没有品尝过”的大学生特罗菲耶夫。在一群商人、贵族、奴仆中间,需要一个大学生,作为新时代的观察者和预言者,自尊、悲悯而又开阔。契诃夫大概把自己的形象转移到这一人物身上,甚至连特罗菲耶夫父亲的身份,都被写成了“药剂师”。
宝庆路附近有上海戏剧学院,我在学院剧场中看过日本现代舞《樱之园》,依据契诃夫的《樱桃园》而改编:
一座老房子面临拆迁,庭院中的樱花树怎么办?房主,一个不成器的人,对于樱花树感情淡漠,为避免缴纳高额遗产税而催促拆迁公司速速行动。但,护绿会的一个姑娘却誓死保护樱花树。女演员在舞台上激烈跑动,围绕一棵产权与自己无关的樱花树,跑动着,呼吁着。最终,护绿会姑娘,女演员,在渐渐黯淡的追光灯中安静下来,樱花树倒了下去。她说着自己的故乡和丧失,充满哀愁。帷幕后,隐隐响起了日本自卫队战机的轰鸣声,呼应于俄罗斯的斧声、火车汽笛声。
俄罗斯的樱桃树,就是日本的樱花树、上海的玉兰树,在充满了被丧失、被斫伐的危险预感中,楚楚动人——
“靠近亭子的地方,有一棵白颜色的树,树干弯了,像个女人。”
“亲爱的、尊贵的书柜,我向你致敬,在一百年的时间里,你一直为善良和正义而服务。”
“你需要的不是看戏,而是看自己,你活得多没有味道,你说了多少废话。”
“生命好像完结了,可我好像还没有生活过。”
“大自然,神奇的大自然,闪耀永恒的光,那么美丽、超脱,你,我们称之为大自然母亲,包容生死,你给予生命,也能将它毁灭。”……
《樱桃园》中的这些台词,充满了诗意和感染力,完全像宝庆路三号内的老克勒们在独白或者对白——必须有能力触动灵魂和记忆,一个句子、一棵树,才能够活下去。
7
小说家汪曾祺把明代作家归有光比作“中国的契诃夫”——那么,我可以把契诃夫比作“俄国的归有光”?两人的共同点都是:留白,爱闲笔,抒情,对讲故事没有大兴趣——这其实就是诗人气质,《樱桃园》中的大学生特罗菲耶夫的气质——“一种模糊而美丽的人类真理的担负者,不幸的是,他对于这一重负既卸不下,也担不动”,纳博科夫如此评论契诃夫笔下的这一人物。
高尔基同样敬重契诃夫,说,他好像是站在路边微笑着对走过的人们呼吁:“你们可不能再这样活下去了。”但在宝庆路三号、在上海、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没有听见,或者假装没有听见这一呼吁。没有听见,或者假装没有听见,才能心安理得地过一种没有精神负担的生活,走肉如行尸。
青年时代,我与同事常常在办公室值夜班、看电视剧。一个晚上,某领导走进来:“什么电视剧?”同事恭敬地站起来回答:“《不知其名》。”领导看了同事一眼,走了。五分钟后,同事抱着脑袋蹲在了地上,满脸通红,问我:“领导误会我了吧?”我不解:“怎么了?”同事嘀咕:“领导问我什么电视剧,我说《不知其名》,他看了我一眼——可能以为我在用书面语‘不知其名’搪塞他吧?真邪门啊,这个破电视剧的名字……”
遂想起契诃夫的小说《小公务员之死》。当然,我的这一个同事没有死,后来混成了某一级别的官员,开始让后辈小职员来揣摩、不安。我们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完成了对天真的背叛,庸俗地活下来了。
写完《樱桃园》不久,契诃夫活不下去了,在德国疗养地去世,像被死神伐倒的一棵樱桃树。运回俄国的棺材,竟然装在一节写着巨大“牡蛎”字样的货运车厢里,被心痛气急的亲人们找了半天才找到——契诃夫想变成一只牡蛎?火车站台上,一支假装悲伤的乐队在节奏缓慢地演奏催泪曲,但与契诃夫无关——那哀乐,献给同一列车运回的某个俄国将军的遗体。
如此荒诞的场景,像契诃夫虚构出来被演出的最后一台戏,以火车作为舞台背景。
上海也是舞台。人间无处不舞台,但道具中已经出现了高铁、地铁、磁悬浮列车、飞机。我应该尽量避免成为种种舞台上一个可笑、可悲的角色,即便身份再微乎其微、台词再有限,也应该站在那一个似乎永远无法毕业的俄罗斯大学生身边,站在樱桃树、樱花树和玉兰树一边。
归有光在《项脊轩记》里,对一棵树念念不忘:“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需要一棵自己的树来寄托身与心。但即便能找到这样一棵树,也难以摆脱可怜、可叹息的境地?
8
徐元章书房的吊灯上,三条链子中的一条已经断了,灯光暂时没有倾斜。
维护这样一个院落,耗资巨大。徐元章请花匠隔日来打理一次花园。把各色灯泡换成乏味的节能灯。冬夏时节独自在家,也少开或不开空调。
徐元章在纪录片中展示了父亲徐兴业的长篇小说《金瓯缺》。还有一沓信札,是父亲早年写给母亲周润琴的情书。书和信札,残存着父母日益抽象、稀薄的心跳和手温。
《金瓯缺》起笔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以南宋时期抗金斗争为背景,塑造了民间义军领袖马扩的英雄形象,显然是对抗日战争这一当时社会主题的回应。徐兴业在完成前三卷后,中断写作二十余年,直到八十年代才匆忙完成第四卷,收束全书。我想探究这一前后绵延四十年的写作,究竟出现了哪些动力与障碍?是否与其爱情的发端与了结有关?书中是否出现了个人私密情感的投影?从上海图书馆借来《金瓯缺》,读毕,似乎印证了一些猜测。
无锡国文专科学校毕业生徐兴业,被周宗良请来,为中学生周润琴讲授历史和古诗词。一个其貌不扬、家境困窘的青年教师,遇见了一位好姑娘——跳芭蕾、画油画、向往革命、尝试跑到苏北参加新四军,一个大家闺秀爱上寒门书生,这是发生在宝庆路三号的真实故事,而非言情小说中的陈俗虚构。周宗良自然反对将这一“言情小说”写下去。周润琴决然出走,与徐兴业在租住的公寓里结婚,生下徐元章。一九四八年,周宗良迁居香港,徐兴业与周润琴才带着七岁的徐元章搬进宝庆路三号。
《金瓯缺》,也许是徐兴业与周润琴恋爱的副产品。两个人爱着、商量着,推进纸上情节的叙述。前三卷,语调缓慢、沉着,对情节的走向、人物的结局充满底气。第四卷就草率匆促了,像一个故事大纲,写作的倦意难以遮掩——此时,周润琴在徐兴业的生活中已经消失多年。贯穿全书的主人公马扩与其妻赵亸娘的爱情,显然寄托了徐兴业对周润琴的眷恋,热烈得近于夸张,也就愈加失真、可疑。
周润琴自香港去了法国,偶有信件被骑着绿色永久牌自行车的上海邮差,投入宝庆路三号门口的邮箱。后来,她像失联的飞机,连一个机翼碎片都没有留下来以供猜测和追寻。
《樱桃园》中家庭教师夏尔洛塔的有些台词,完全像徐兴业的自言自语:“我什么也不知道,真想找个人说说话,但找不到了……”
9
徐元章的长相、气质酷似父亲徐兴业,连爱情故事也在复制父母之间情感的起、承、转、合,显得缺乏想象力。他与妻子黄亨义的爱,也发端于师生恋。黄亨义多才多艺,曾经是京剧演员言慧珠、歌剧演员温可铮的学生。她的美,被当时很多人求爱追从。最终,还是在一九七一年嫁入宝庆路三号——不知道这个庭院在黄亨义心中的分量,是否超过了徐元章。一九九二年,黄亨义带着女儿去了美国,渐渐也没有了消息。
徐元章一生活动范围没有超出上海。他对自家篱笆外的世界不感兴趣,对十字路口次第变幻的时代潮流也充满惧意。但他必须迎接世界和时代的种种敲门声——温和的、试探的、淡漠的、咄咄逼人的。幼年学习画画,也都是母亲请人来宝庆路三号上门授课——教师就是后来声名赫赫的雕塑家、油画家张充仁和肖像画大师俞云阶。
徐元章似乎把所有才华和力量,都用于追忆。“所有的艺术都是追忆。最好的艺术是对未来的追忆。”(查尔斯·赖特)所以,艺术家是非现实的人——被现实排斥越强烈,对未来越不安,就越杰出。除了老房子,徐元章什么都不画。名气渐渐大了,被美国《时代周刊》等媒体报道。不少外国人来宝庆路三号看画、买画。瑞典驻上海领事馆曾经在此举办过“瑞典之夜”的聚会,近两百位中外人士萃集于草坪,灯火辉煌,小乐队演奏着小夜曲……
不久前,我在中华艺术宫看了徐元章遗作展:几十座别墅耽溺于水粉中,陈旧而又艳丽,像一群与上海人存在时差的异邦游客,像与现实存在隔膜的德式、法式、英式、美式的徐元章。
中华艺术宫就是二○一○年世博会期间的中国馆。
10
上海大约有五千余幢悬挂“历史保护建筑”字样铭牌的洋房花园,如思南公馆、哈同花园、丁香花园、沙逊别墅、马勒别墅、爱庐别墅、爱神花园、绿房子、望庐、宋家花园、荣公馆、白公馆、张公馆、犹太人总会、嘉道理住宅、华业大楼……密布于外滩、南京路、淮海路、华山路、湖南路、新华路、复兴西路、汾阳路、太原路等地段,繁华之中存大幽静。从事老洋房交易的一个律师朋友,曾对我分析其中规律:晚清至民国时期,官员大多居住于徐汇区,商人大多居住于静安区,文人、学者、专家大多居住于黄浦区。
我探访过其中部分院落,似乎都种有玉兰树。五月,玉兰盛开,像一树树鸽子迎风翻飞。上海市花就是玉兰。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这些院落大部分归于国家,成为博物馆、少年宫、学校、餐馆、音乐学院琴房、作家协会办公地,等等。旧人已去春常在,玉兰兀自开。这些异国风格的院落,组合出上海混血的面貌。墙里秋千,可能早已拆掉。墙外单行道上车流汹涌,行人们匆匆奔向证券交易所、草地音乐会、大师赛、主席台、饭局、家长会、新概念作文比赛、机场、财务负债表、法庭、离婚协议、告别仪式……墙里旧照片中的民国佳人,隐隐笑。
部分花园别墅成为各阶层市民混居的公寓。即便在特殊年代,这些建筑内的部分人物,面容与身影依然保持旧生活的夕照余晖:女子们悄悄去锦江饭店里做发型,穿自己改良之后的“列宁装”“布拉吉”,走在路上像安娜·卡列尼娜一样引人注目;男士去照相馆,脱下千篇一律的蓝色工作服,从提包里掏出珍藏已久的西装,系上领带,坐对光芒;回家,在厨房里揣度西式糕点的配方,阅读包着红色书皮的西方文学名著……
存在一个看不见的上海,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好眼力、好笔力,也看不见、写不出的上海。
建筑、环境就是命运——彩绘玻璃窗上一个天使图案的飞翔,仆人夜半走廊上的偷窥,室内楼梯或街头拐角处的身体碰擦,弄堂里的一次凝眸和落日,十字街头的一次转身和细雨……都可能引发出一个情节、一个事件,让生息其中的人拥有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高潮和结局。“一个以密切交织的人际关系为特征的生活世界,在里弄房屋内呈现出来。有时候,激情也会公然迸发,而欲望则流动于街道、小巷、菜场构成的无数迷宫之中。”李欧梵在对金宇澄小说《繁花》的评论中,谈到了上海地理与人性幽明之间的关系。
显然,一个人对于所处空间的态度,就是世界观、价值观。服从它、眷恋它或者逃脱它,就是一部小史诗——杜甫的茅屋和身体,必然为秋风所破;归有光的项脊轩和枇杷树,必然归于苏州城外名为“项脊泾”的一片田野;徐元章的老洋房和玉兰,也只能被资本和时间有力主宰。
11
徐元章画作。
在徐元章的画笔下,我看见两个熟悉的院落。
其一,铜仁路与北京西路交叉形成的十字街头,一座四层别墅式酒吧“艳阳天”。初为上海滩另一个颜料大王吴同文的私宅,因外墙微绿而俗名“绿房子”。吴同文是当代建筑大师贝聿铭的姑父,与周宗良之间存在复杂的竞合关系。绿房子在当年上海滩巨富大亨们的豪华宅邸排行榜上,也曾位居前列:小电梯首次出现于上海家庭,客厅地面铺设弹簧板以增强跳舞时的足部快感……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曾经来访,与吴同文在二楼阳台共进晚餐。吴同文与妻子死于上世纪六十年代。
绿房子,就是吴同文的“樱桃园”?
我曾经进入艳阳天酒吧或者说绿房子,与一个战略合作伙伴达成共识。透过窗子,庭院里也有一棵开满白花的玉兰树,“树干弯了,像个女人”。
另一个院落,是愚园路上由三座小楼围合而成的花园。
院落原主人为民国时期一家医药企业的老板。上世纪五十年代公私合营后,该院落成为我所供职的一个国家级药物研发机构的组成部分。主人的儿子,王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从英国留学归来,成为这一院落里的科学家,童年时代的卧室成为了他的实验室。王先生的妻子是留学期间在伦敦街头遇见的一位好姑娘,后在复旦大学教书。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许多夜晚,为解决涉及有毒气体的若干工艺路线研究,王先生独自在这一院落内的草地上点亮蜡烛,露天工作,摆弄着试管、烧瓶、试剂——当时的实验室内通风条件比较差,只能借助于室外晚风的吹拂。
后来,王先生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数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级大奖。为了药物工艺研究所需要的手感、灵活度,他买了一个理发推子,与自己的研究生相互理发——王先生和研究生们的发型,都显得简单、稚拙、朴素。目前,王先生九十多岁了,住在一栋高层公寓内,墙壁上悬挂着他书写的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妻子不久前患了失忆症,除了王先生,对这个世界上的山重水复,对这座城市里的花园菜场,一概丧失了认知和牵挂。除非入睡,当王先生做事情,她就坐在一旁安静地看着丈夫,一眼不眨,寸步不离。“去复去兮如长河啊——白居易的诗吧?这是在说晚年。杨万里这首诗,说的是青春壮年——堂堂溪水啊,堂堂溪水……”王先生对前来登门探望的我如此感叹。他喜欢写旧体诗。他谅解写自由体诗的我:“自由,不容易——河流在两岸的约束中才能入海啊。可我,我们这代人,又似乎被约束过多……”
王先生茶几上有契诃夫和鲁迅的小说。“他们都是医生出身,我是药物学家——药物和医学算是知己、邻居?应该能谈得来,呵呵……”
我问王先生知道宝庆路三号吗?他点点头。知道徐元章吗?他摇摇头。王先生高大硬朗,与徐元章的气质和趣味迥然不同。在上海,拥有旧贵族背景的人们像不同的鱼群,在不同温度的海域里,各自游动。
我告诉王先生,他以前的家、后来的实验室,被徐元章“搬”进了画框。王先生笑了:“他在审美,我在研究,都好,都需要。能在自己出生的房间里做科学实验,是很难得、很奇妙的事情呀,圆满,满足——太棒了!”他端起咖啡杯,向我举了举。
12
宝庆路三号外是公交汽车站。乘坐公共汽车的人们,漠然背对这一庭院。他们只向公交车所代表的大致相似的动机、契机、转机,殷殷眺望——那公共的、平民化的未来。
个性化的、别致的前途命运,暗藏于旧时代的马车、火车,新时代的兰博基尼、法拉利等汽车,或丽娃、阿兹慕等豪华游艇,或首相一号、豪客等私人飞机。大同小异,万象归一——归于短暂的欢愉、长久的隐疾与剧痛,以至最终的平静。
我数次有意前来或无意中路过,都没有看见宝庆路三号内的玉兰树。它们每一年都在新生,不论庭院里的主与仆如何更迭衰荣,永远只对春风和光线来发芽、发言。
像上海的玉兰、日本的樱花树、俄罗斯的樱桃树一样,契诃夫永远不会过时——好作家像新人、亲人、友人,在同一时空与我们生息相伴。当一个人病了,契诃夫们就会捏着一纸药方、一支温度计,出现在无影灯下、病床边、走廊里,以及书桌上那一个酷似药罐的墨水瓶旁。
汗漫,作家,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一卷星辰》《南方云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