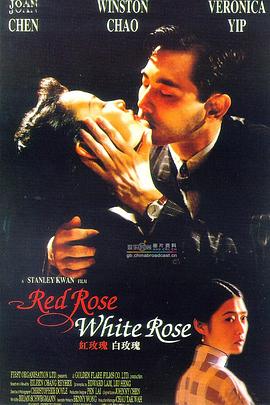剧情介绍
2018年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0周年的日子。中国大荧幕上数部影片进入院线放映,也让我们在那个秋天看到了这部在中国张家界取景的《镰仓物语》。
央视六套近期在《今日影评》中提及影片中不少形象是《山海经》东渡后的形象,比如从中国的河伯变成日本的河童等等。进而提出日本对于自身传统文化的保护等相关的话题。
影片观摩之后,更为显著的印象是影片化用了希腊神话与亚洲文化。这种创作的形式非常具有参考价值。从唐以来的“和魂汉才”到日本的圣德太子开始主张的“和魂洋才”,日本走上了和其他亚洲国家不太一样的发展之路。从此,日本文化里:早先唐宋影响的,近代欧美影响的,和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杂糅交融。笔者试从跨文化视角,就《镰仓物语》谈三点看法 :
和风版的俄耳浦斯追妻
死而复生的想法在古老的文化里,由于早期人类的理解局限而存在。所以,看着尼罗河的涨落,天狼星的升降,埃及人觉得死者将会复生,法老还会归来。放在进入蒸汽时代而成立的国家、社会,死亡是一条单行线。所以,哪怕如《寻梦环游记》,那也只是去了一个“异次元”空间的旅行,本质上和《蚁人2》里去了一次量子空间,《火星援救》里去了一次火星差不多。但基本的认同还是:死了就是死了,不可能再回来——coco是到了亡灵城,而不是反向的从亡灵城回来一个coco他爸。
在德国人古斯塔夫整理的《希腊神话》里有这样一个优美而悲伤的故事。前半段是古希腊人延续埃及文化影响,对于死亡之后复生的幻想:太阳神阿波罗的儿子俄耳浦斯英俊潇洒,一把琴弹得旷古绝今。他的妻子是美丽的欧律狄刻,两人恩爱无比。然而一次意外欧律狄刻被蛇咬,死去了。俄耳浦斯追到地府,用琴声打动了哈德斯夫妇。冥王都为之动容,答应让他带着妻子离开冥府。而后半段,更像是德国人或者是西方理性源头的希腊人对于死亡的认知:俄耳浦斯由于没有遵守约定,而导致最终妻子还是留在了地府,阴阳两隔。
这种“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情节,在中国故事里,有大圣来到阎罗殿修改阳寿,也有包大人在阎罗殿研判冤案。不过,到黄泉寻爱找老婆的,似乎希腊人占了先机——这个理由发生在希腊也不稀奇,毕竟一部《希腊神话》里,这类故事不甚枚举。
俄尔普斯下地府寻妻的动机和影片中追妻来到黄泉一模一样——不希望妻子就这样离开自己。为了让追妻显得合理,影片的前半段描述了两人的恩爱,还介绍了最后要闯关得救的宝贝的由来。特别是通过演员精湛的演技,中途黄泉送别的过程催人泪下,展现了东方人情感的细腻感人。但《镰仓物语》不是《精神病人》,女主虽然中途“死”了,但不代表中途“领盒饭”。影片里,男主人公的逻辑线就是让人信服他深爱妻子,甘愿为他去可能再也回不来的黄泉。
东方的美女与野兽
从男主人公角度发展的故事是“追妻”记,从女主人公发展的故事却是“美女与野兽”。不过这条线展开得有点无厘头。
《美女与野兽》的故事肇始于法国的jeanne-marie leprince de beaumont 夫人,被迪斯尼改编成经典童话的《美女与野兽》享誉全球。这个美貌女性自主选择留下来,并在相处中产生爱情,最后拯救丑陋野兽的故事,被女权主义者解读为女性的觉醒。显然仰慕法国的日本人仰慕的只是外表——《镰仓物语》里,丑陋的野兽,灵魂也丑陋。美貌的女性哪怕住了一段时间,也没有产生爱情——或者说在冥府的时间只是“历劫”。她还是需要等待男主的拯救,一切的美好还是因为这是前世注定的缘分——故事里最大的逻辑bug也出于此:不论是天头鬼还是男主,都是女主的前世爱人。只不过“天头鬼”是更早几世的爱人(剧情说:天头鬼因为没有忘记前世的故事,所以从中作祟),而从上一世开始,女主的命定之人成了容貌英俊的三浦友和版的爸爸和堺雅人的男主。换句话说,女主水性杨花,移情别恋了。
这种强调“生生世世”的美好,与去年大热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在陈述“真爱”的理由时是一样的——也许有自主的爱,但更多是因为“上辈子,上上辈子我们就在一起。所以我们理所应当的应该再在一起。”影片似乎要表达男主和女主是“命中注定的爱情”,而天头鬼是“强扭的瓜不甜”,一种东方的“无为”由此而起。但有趣的是,《镰仓物语》告诉我们,如果后来不能在一起,一定是因为“你长丑了。”
虽然电影没交代女主与天头鬼相爱的时候的容貌,但从上一世开始就换了英俊的三浦友和的时候,那一届恋人到没有讨论“命中注定”的恋爱,这就和影片的设定产生了一些矛盾,所谓bug由此而来——男主和女主究竟为什么相爱?难道只是因为容貌?或者是有阻挠而产生的“罗密欧朱丽叶效应”?——何况这个阻挠的丑八怪还这么凶恶,但如果“天头鬼”貌比潘安,还痴心不改,这样的时候,男主和女主还一心所求在一起,看起来才比较像真爱。
而从中推导出“失去了爱情就是丑八怪”这个论点,虽然不一定是电影里想表达的本意。但对于注重表面、注重物化的日本文化内核,倒是一个潜意识的外部展现。而且高票房似乎侧面说明,这种展现是符合日本人内心所想的。
镰仓的百鬼夜行图
这部影片的男女主人公,恰似东西方文化的两个模式,在古都镰仓开始了一段奇幻之旅。虽然整个故事的设定飘忽有鬼气,但这种鬼气尚且是亚洲的,东方的,换句话说似乎这个层面上,别的亚洲国家也还能拍。但影片的日本痕迹在于,不仅保留了早先日本和化了《山海经》神鬼意象,更和《千与千寻》一起,不约而同的使用到了铁道的意象——这恰是来自日本本土大作家宫泽贤治,他的作品翻译成14种语言为世人所熟悉。在他的《银河铁道之夜》里贡献给日本文化的一个经典符号——死亡铁道。1855年,佐贺藩自主建成酒精蒸汽机车模型,并在轨道上试行成功。1872年10月14日,日本第一条铁路—新桥(在当时为包含汐留在内的泛称)至横滨(车站约位于现在的樱木町站)间约29公里的铁路正式通车,成为明治维新的重要成就之一。
蒸汽时代的标志“铁道”与东方文化的概念“阴阳两界”的组合,让人对于影片产生强烈的“日本感”。这既不是《寻梦环游记》里的菊花桥,也不仅仅是中国文化里的黑白无常索命,形式上有工业感,精神上又有强烈东方味的影片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
来往与人界和黄泉的摆渡火车寓意的“死而复生”,是和俄尔普斯、coco这些代表的西方文化、拉美文化完全不一样的东方的生死观。尽管美国人用《魔弦传说 》也讲了一个日本与死亡有关的故事。但美国人讲的日本故事,和日本人讲的日本故事,差异就在于不同的文化背景看待生死。
影片里当然不是一部杰作,优秀的地方之外,存在着诸如略生硬的细节铺成、支线的裁剪失当,当然也包括没有深度的主题等一系列的问题,但是作为一部多文化融合,讲述本国故事的故事片,对于同等类型影片的创作者而言,是一个可以学习、反思的对象。